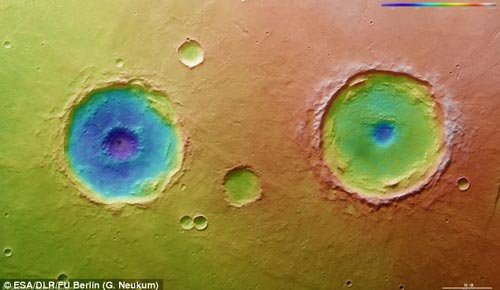зҝ»иҜ‘д№Ӣи·Ҝ и·ҜеңЁдҪ•ж–№ | 2013-06-12 10:28:33 (иў«йҳ…иҜ» 1026 ж¬Ў) |  | дёӯеӣҪжҳҜзҝ»иҜ‘еӨ§еӣҪпјҢзҝ»иҜ‘зҗҶи®әеҚҙзӣёеҜ№ж»һеҗҺпјҢе…ідәҺзӣҙиҜ‘дёҺж„ҸиҜ‘гҖҒеҪўдјјдёҺзҘһдјјзӯүиҜёй—®йўҳеӨҡжңүдәүжү§гҖӮеӮ…йӣ·дё»еј вҖңйҮҚзҘһдјјдёҚйҮҚеҪўдјјвҖқпјҢйІҒиҝ…еҲҷжҸҗеҮәвҖңе®ҒдҝЎиҖҢдёҚйЎәвҖқпјҢеӣ дёәиҜ‘жң¬вҖңдёҚдҪҶеңЁиҫ“е…Ҙж–°зҡ„еҶ…е®№пјҢд№ҹеңЁиҫ“е…Ҙж–°зҡ„иЎЁзҺ°ж–№жі•вҖқгҖӮдёӨз§Қдё»еј пјҢеқҮдёҚд№ҸиҝҪйҡҸиҖ…гҖӮеҪ“дёӢпјҢеҸ—еёӮеңәеӣ зҙ еҪұе“ҚпјҢеҸҲеҮәзҺ°дәҶдёҚе°‘ж–°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йҮҚеӨҚзҝ»иҜ‘гҖҒд»Ҙж¬Ўе……еҘҪзӯүзҝ»иҜ‘д№ұиұЎдёӣз”ҹвҖ”вҖ”
зҝ»иҜ‘д№Ӣи·Ҝ и·ҜеңЁдҪ•ж–№
гҖҖгҖҖжұҹжһ« иҜ—дәәгҖҒеӯҰиҖ…гҖҒзҝ»иҜ‘家пјҢеҺҹеҗҚеҗҙдә‘жЈ®пјҢз”ҹеңЁдёҠжө·пјҢзҘ–зұҚеҫҪе·һгҖӮжӣҫе°ұиҜ»дәҺжё…еҚҺеӨ§еӯҰеӨ–ж–Үзі»е’ҢеҢ—дә¬еӨ§еӯҰдёӯж–Үзі»гҖӮ1949е№ҙ2жңҲеҸӮеҶӣпјӣ1951е№ҙеҪ“йҖүжұҹиҘҝзңҒж–ҮеҚҸйҰ–еұҠ常委пјӣ1956е№ҙе…ҘеҢ—еӨ§пјҢеҸӮдёҺеҲӣеҠһгҖҠзәўжҘјгҖӢжқӮеҝ—пјӣ1978е№ҙеңЁеҢ—дә¬еҜҶдә‘еҲӣеҠһгҖҠеҜёиҚүгҖӢжқӮеҝ—пјӣ1983е№ҙ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дёүSз ”з©¶дјҡеҲӣе§ӢеёёеҠЎзҗҶдәӢпјӣ1995е№ҙиҺ·еҫ—жҲ‘еӣҪйҰ–ж¬Ўи®ҫзҪ®зҡ„еҪ©иҷ№ж–ҮеӯҰзҝ»иҜ‘з»Ҳиә«жҲҗе°ұеҘ–пјӣ1996е№ҙиў«иҒҳдёәжё…еҚҺеӨ§еӯҰеӨ–иҜӯзі»е…јиҒҢж•ҷжҺҲгҖӮиҷҪжңүиҜ—ж–Үй—®дё–пјҢе°Өд»ҘиҜ‘йӣӘиҺұгҖҒзӢ„йҮ‘жЈ®гҖҒеҸІжІ«зү№иҺұй—»еҗҚпјҢеҫ—ж„Ҹд№ӢдҪңеҚҙжҳҜгҖҠжұҹжһ«и®әж–ҮеӯҰзҝ»иҜ‘еҸҠжұүиҜӯжұүеӯ—гҖӢпјҢжңүиҮӘжҲҗдҪ“зі»зҡ„иҜ‘и®әгҖҒжңүж–Үеӯ—з ”з©¶зҡ„зӘҒз ҙпјҢжңүеҜ№еҪ“д»Ҡж–Ү科ж•ҷиӮІејҠз«ҜжңүеҠӣзҡ„й’Ҳз ӯгҖӮ2011е№ҙпјҢиҺ·дёӯеӣҪзҝ»иҜ‘ж–ҮеҢ–з»Ҳиә«жҲҗе°ұеҘ–гҖӮжҷҡжқҘйӣ…зҲұзӢ ж–—еӯҰжңҜи…җиҙҘпјҢиҮӘд»ҘдёәиҚЎж¶Өжғ‘дј—еҰ–иЁҖпјҢиҠӮзәҰж•ҷиӮІиө„жәҗгҖҒйҒҝе…Қз”ҹе‘ҪжөӘиҙ№пјҢ并且пјҢжңүеҠ©дәҺжҒўеӨҚжҲ–еўһејәеӯҰжңҜз•Ңзҡ„иҮӘеҮҖиғҪеҠӣгҖӮ
зҝ»иҜ‘еҸҜд»ҘзҷҫеҲҶд№Ӣзҷҫеҝ е®һеҗ—пјҹвҖ”вҖ”еҶҚй©ізҝ»иҜ‘жҖ»жҳҜвҖң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вҖқ
в–Ў жұҹ жһ«
гҖҖгҖҖв—ҺжңүзҗҶжғізҡ„зҺ°е®һдё»д№үиҖ…пјҢиҝҪжұӮзҗҶжғіпјҢжҺҘеҸ—зҺ°е®һпјҢдёҚжӯўжӯҘдәҺзҺ°е®һгҖӮиҝҷз§Қеҝ е®һд№ҹи®ёе°ұжҳҜеҫ·зҗҶиҫҫзҡ„пјҡеҝ е®һзҡ„дёҚеҝ е®һпјҢдёҚеҝ е®һзҡ„еҝ е®һгҖӮжңүдәәеҗҰе®ҡзҝ»иҜ‘иғҪжңүе®ҡжң¬пјҢиҝҷе°ұжҳҜе®ҡжң¬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иғҪд»ҘжӣҙеҘҪзҡ„иҜ‘жң¬еҠ д»Ҙд»ЈжӣҝпјҒ
гҖҖгҖҖдёәдәҶејҖеҘҪвҖңжұҹжһ«е…Ҳз”ҹе…«еҚҒеҚҺиҜһеӯҰжңҜз ”и®ЁдјҡвҖқпјҢзӯ№еӨҮз»„иҰҒжҲ‘жҠҠеҮ жң¬еҮәзүҲзӨҫдёҚж•ўеҮәзҡ„и®әж–ҮйӣҶпјҢжҠҪйҖүдё»иҰҒйғЁеҲҶеҗҲжҲҗдёҖжң¬иҮӘиҙ№еҮәзүҲгҖӮиҝҷжң¬д№ҰйҮҢжңүдёӨзҜҮжү№иҜ„йғҪе’Ңи°ўеӨ©жҢҜж•ҷжҺҲзҡ„гҖҠиҜ‘д»ӢеӯҰгҖӢжңүе…ігҖӮйӮЈвҖңиҜ‘д»ӢеӯҰвҖқ究з«ҹжҳҜдёҚжҳҜеӯҰй—®пјҢеҰӮжһңжҳҜпјҢеҸҲ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жҲ‘и®ӨдёәжҳҜдјӘзҝ»иҜ‘еӯҰпјҒеӣ дёәиҝҷз§ҚжүҖи°“вҖңзҗҶи®әвҖқзҡ„ж ёеҝғи§ӮеҝөпјҢжҳҜжңүжӮ–дәҺдәӢе®һзҡ„жүҖи°“вҖңзҝ»иҜ‘жҖ»жҳҜдёҖз§Қ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вҖқпјҢд»–д»ҘжӯӨдёәи®әжҚ®пјҢеҸӘеӣ дёә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еӨ–еӣҪдәәжүҖиҜҙгҖӮиҖҢи°ўеӨ©жҢҜзҡ„вҖңи®әиҜҒвҖқеҲҷжҳҜпјҡвҖңзЎ®е®һпјҢеңЁеҸӨд»ҠдёӯеӨ–зҡ„ж–ҮеӯҰеҸІдёҠпјҢжӯЈжҳҜж–ҮеӯҰзҝ»иҜ‘зҡ„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пјҢжүҚдҪҝеҫ—дёҖйғЁеҸҲдёҖйғЁзҡ„ж–ҮеӯҰжқ°дҪңеҫ—еҲ°дәҶи·Ёи¶Ҡең°зҗҶгҖҒи¶…и¶Ҡж—¶з©әзҡ„дј ж’ӯе’ҢжҺҘеҸ—гҖӮвҖқиҝҷз§Қе…Ёз§°иӮҜе®ҡпјҢеҸӘиҰҒжңүдёҖдёӘеҸҚиҜҒдҫҝи¶ід»ҘжҺЁзҝ»пјҢдҪ•еҶөпјҢеҸӨд»ҠдёӯеӨ–ж–ҮеӯҰеҸІдёҠеҰӮдҪ•еҰӮдҪ•е°ұжҳҫ然жҳҜи°ҺгҖӮи°ҒзӣёдҝЎд»–иҜ»иҝҮвҖңеҸӨд»ҠдёӯеӨ–ж–ҮеӯҰеҸІвҖқпјҹиҝһдёӯеӣҪж–ҮеӯҰеҸІйғҪжңӘеҝ…иҜ»иҝҮпјҢеҗҰеҲҷе°ұдёҚдјҡжҠҠгҖҠйҹ©иҜ—еӨ–дј гҖӢзҡ„еҗҚеҸҘпјҢвҖңиҜҜиҜ‘вҖқдёәвҖңж–Үйқ©ж—¶жңҹеҲӣйҖ зҡ„ж”ҝжІ»жү№еҲӨиҜӯ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зј–еҶҷгҖҠиҜ‘д»ӢеӯҰгҖӢж—¶пјҢи°ўеӨ©жҢҜж•ҷжҺҲеҸӘжүҫеҲ°дёҖдёӘеҸӣйҖҶзҡ„жҲҗеҠҹвҖңдҫӢиҜҒвҖқпјҢиҜҙвҖңзІҫйҖҡиӢұж–Үзҡ„й’ұй’ҹд№ҰпјҢе®ҒеҸҜиҜ»жһ—зәҫзҡ„иҜ‘ж–ҮпјҢдёҚж„ҝж„ҸиҜ»е“Ҳи‘ӣеҫ·зҡ„еҺҹж–ҮпјҢзҗҶз”ұеҫҲз®ҖеҚ•пјҢжһ—зәҫзҡ„дёӯж–Үж–Ү笔жҜ”е“Ҳи‘ӣеҫ·зҡ„иӢұж–Үж–Ү笔й«ҳжҳҺеҫ—еӨҡвҖқпјҢд№ҹдёҚзҹҘиҝҷдёӘдёӯж–Үж–Ү笔е’ҢиӢұж–Үж–Ү笔зҡ„й«ҳдҪҺжҳҜжҖҺж ·жҜ”зҡ„пјҹиҝҷдёӘй«ҳдҪҺжҳҜд»–иҮӘе·ұжҜ”еҮәжқҘзҡ„пјҢжҠ‘жҲ–еҸӘжҳҜйҒ“еҗ¬йҖ”иҜҙпјҹдҪ•еҶөпјҢд»ҺдёҚжҮӮеӨ–ж–Үзҡ„жһ—зәҫ笔дёӢдә§еҮәзҡ„дјҡжҳҜвҖңиҜ‘ж–ҮвҖқд№ҲпјҹдҪҶжҳҜжӯӨиҜҙжңүз”ЁпјҢд»–е°ұи®°дҪҸдәҶпјҢиҖҢдё”пјҢиҰҒжұӮеҲ«дәәзӣёдҝЎгҖӮ
гҖҖгҖҖзңҹжӯЈзҡ„еӯҰиҖ…пјҢиҰҒд»ҘжӯӨдёәжҚ®иҝӣдёҖжӯҘжј”з»ҺжҺЁзҗҶпјҢе°ұиҜҘйӘҢиҜҒдёҖдёӢй’ұй’ҹд№Ұзҡ„иҜқжҳҜеҗҰеҸҜйқ пјҢиҮіе°‘еә”иҜҘзҹҘйҒ“е“Ҳи‘ӣеҫ·жҳҜи°ҒпјҢиҜҙзҡ„жҳҜе“ӘзҜҮжҲ–е“ӘйғЁи‘—дҪңпјҢй’ұй’ҹд№ҰжҳҜеҚ•зӢ¬й’ҲеҜ№е“Ҳи‘ӣеҫ·пјҢиҝҳжҳҜдҪҶеҮЎжңүжһ—иҜ‘е°ұдёҚиҜ»еҺҹж–ҮпјҢд»ҘеҸҠпјҢдё–з•ҢдёҠзҡ„й’ұй’ҹд№ҰжңүеӨҡе°‘пјҢжүҖжңүзҡ„иҜ»иҖ…йғҪжҳҜй’ұй’ҹд№Ұд№ҲпјҹйҖ»иҫ‘пјҢе°ұжҳҜиҰҒйҒҝе…ҚжҲ‘们иғЎжҖқд№ұжғігҖӮ
гҖҖгҖҖ姑дёҚи®әжӯӨдҫӢиғҪеӨҹиҜҙжҳҺд»Җд№ҲпјҢеҚҒеӨҡе№ҙжқҘд»–иӢҰиӢҰжҗңеҜ»пјҢд№ҹжңӘиғҪеӨҹжүҫеҲ°з¬¬дәҢдҫӢпјҢиҝҷж¬ЎиҺ«иЁҖеҫ—еҘ–пјҢи°ўеӨ©жҢҜеҰӮиҺ·иҮіе®қгҖӮзңҹжҳҜд»ҒиҖ…и§Ғд»ҒпјҢжҷәиҖ…и§ҒжҷәпјҢи°ўеӨ©жҢҜи§ҒвҖң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вҖқгҖӮ
гҖҖгҖҖ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и°ҒйғҪзҹҘйҒ“гҖӮиҺ«иЁҖжӯӨж¬ЎиҺ·еҫ—еӣҪйҷ…ж–ҮеӯҰз•Ңзҡ„еӨ§еҘ–вҖ”вҖ”иҜәиҙқе°”ж–ҮеӯҰеҘ–пјҢдёҺзҝ»иҜ‘жңүзқҖйқһеёёеҜҶеҲҮ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е…¶иғҢеҗҺжңүдёӘзҝ»иҜ‘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然иҖҢеҚҙдёҚжҳҜи°ҒпјҲеҢ…жӢ¬еӣҪеҶ…зҡ„зҝ»иҜ‘з•ҢпјүйғҪжё…жҘҡе…·дҪ“жҳҜдәӣд»Җд№Ҳж ·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вҖқеҸӘжңүд»–жҳҺзҷҪпјҢдҪҶжҳҜд»–зҡ„жҳҺзҷҪиҜқжҖ»зҰ»дёҚејҖи°Һ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ж—ҘеүҚиҜ»еҲ°дёҖдҪҚиҖҒзҝ»иҜ‘家еңЁиҺ«иЁҖиҺ·еҘ–еҗҺжүҖиҜҙзҡ„дёҖз•ӘиҜқеҚіжҳҜдёҖдҫӢпјҢд»–еҜ№зқҖи®°иҖ…еӨ§и°ҲвҖҳзҷҫеҲҶд№Ӣзҷҫзҡ„еҝ е®һжүҚжҳҜзҝ»иҜ‘дё»жөҒвҖҷгҖҒиҰҒвҖҳйҖҗеӯ—йҖҗеҸҘвҖҷең°зҝ»иҜ‘зӯүдјјжҳҜиҖҢйқһзҡ„иҜқгҖӮвҖқеҸҜжҳҜпјҢиӢҘйқһвҖңйҖҗеӯ—йҖҗеҸҘвҖқе°ұиҝһдёҖдёӘwhatйғҪдёҚзҹҘиҜҘжҖҺд№ҲиҜ‘пјҢдёҚжӯўжҳҜи°ўеӨ©жҢҜпјҢеҢ…жӢ¬жҲ‘пјҢжүҖжңүзҡ„дәәпјҢе…ЁйғҪдёҚзҹҘгҖӮиҝҷиҜқжҳҜжҲ‘2011е№ҙжҺҘеҸ—第дәҢдёӘз»Ҳиә«жҲҗе°ұеҘ–ж—¶еҜ№гҖҠж–ҮиүәжҠҘгҖӢи®°иҖ…иҜҙзҡ„пјҢиҖҢдё”жңүиҜ‘дҫӢдёәиҜҒпјҢдёҖдҫӢжҳҜеЁҒе»үж–Ҝзҡ„гҖҠзәўиүІжүӢжҺЁиҪҰгҖӢпјҡ
гҖҖгҖҖso much depends жңүйӮЈд№ҲеӨҡиҰҒ
гҖҖгҖҖupon дҫқйқ
гҖҖгҖҖa red wheel дёҖиҫҶзәўиүІжүӢ
гҖҖгҖҖbarrow жҺЁиҪҰ
гҖҖгҖҖglazed with rain иў«йӣЁж°ҙж·Ӣеҫ—
гҖҖгҖҖwater жҷ¶дә®
гҖҖгҖҖbeside the white еңЁдёҖзҫӨзҷҪйёЎ
гҖҖгҖҖchickens. иҝ‘ж—Ғ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иҜҙиҝҷиҜ‘ж–Үзҡ„еҝ е®һеәҰдёҚдҪҺдәҺ98пј…пјҢдёҚдҝЎпјҹиҜ·дҝ®ж”№гҖӮеҲ°еӨ©й»‘д№ҹж”№дёҚеҠЁгҖӮиҝҷ98пј…е°ұжҳҜд»ҠеӨ©зҡ„100пј…гҖӮжңүзҗҶжғізҡ„зҺ°е®һдё»д№үиҖ…пјҢиҝҪжұӮзҗҶжғіпјҢжҺҘеҸ—зҺ°е®һпјҢдёҚжӯўжӯҘдәҺзҺ°е®һгҖӮиҝҷз§Қеҝ е®һд№ҹи®ёе°ұжҳҜеҫ·зҗҶиҫҫзҡ„пјҡеҝ е®һзҡ„дёҚеҝ е®һпјҢдёҚеҝ е®һзҡ„еҝ е®һгҖӮеҚіпјҡзҺ°е®һзҡ„еҝ е®һпјҒжңүдәәеҗҰе®ҡзҝ»иҜ‘иғҪжңүе®ҡжң¬пјҢиҝҷе°ұжҳҜе®ҡжң¬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иғҪд»ҘжӣҙеҘҪзҡ„иҜ‘жң¬еҠ д»Ҙд»ЈжӣҝпјҒжҹҗдәәд№ӢжүҖд»ҘиғҪеӨҹдёҖз”ҹиҖҢдёӨиҺ·з»Ҳиә«еҘ–пјҢжҲ‘д»ҘдёәпјҢе°ұжҳҜеҘ–еҠұд»–иҝҪжұӮ并еңЁжҹҗз§ҚзЁӢеәҰдёҠиҫҫеҲ°жҲ–жҺҘиҝ‘иҝҷз§Қеҝ е®һ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иҜҙпјҢиҜ‘ж–Үзҡ„еҝ е®һеәҰиҫҫеҲ°98%пјҢдёҖеҲ»пјҢж”№дёҚеҠЁдёҖдёӘеӯ—пјҢиҝҷ98%пјҢе°ұжҳҜиҝҷдёҖеҲ»зҡ„100%пјҢи°ўеӨ©жҢҜж— жі•еҸҚй©іпјҢзҺ°еңЁеҚҙи„ұзҰ»еҺҹиҜқе…·дҪ“иҜӯеўғе’ҢдҫӢиҜҒжқҘиҜҙвҖңдјјжҳҜиҖҢйқһвҖқгҖӮдёҚпјҢиҝҷжҳҜиҜҙиҜ—жӯҢзҝ»иҜ‘пјҢ100%еҝ е®һдёҚжҳ“пјҢжҲ‘иҜҙиҝҮпјҢиүәжңҜд»ҺжқҘдёҚжҳҜжҮ’жұүзҡ„жёёжҲҸпјҢиҖҢиҜ‘иҜ—пјҢзҺ°е®һзҡ„100%еҝ е®һпјҢз»ҸиҝҮеҠӘеҠӣе°ҡеҸҜиҫҫеҲ°пјҢеҲҷдёҖиҲ¬зҝ»иҜ‘пјҢе°ұжӣҙдёҚеңЁиҜқдёӢдәҶгҖӮеҰӮжһң100%зҡ„еҝ е®һдёҚжҳҜдё»жөҒпјҢ1+2пјҢз»ҸиҝҮзҝ»иҜ‘пјҢеұ…然дёҚзӯүдәҺ3пјҢиҖҢE=mc2пјҢз»ҸиҝҮзҝ»иҜ‘пјҢжүҖиЎЁиҫҫзҡ„з«ҹдёҚеҶҚжҳҜиҙЁйҮҸгҖҒиғҪйҮҸзҡ„иҪ¬еҢ–е…ізі»пјҢдёҚеҗҢиҜӯиЁҖдәәзҫӨд№Ӣй—ҙдҫҝдёҚеҸҜдәӨжөҒдҝЎжҒҜгҖҒжІҹйҖҡжҖқжғіпјҢжҖҺд№Ҳдјҡжңүд»ҠеӨ©жҲ‘们зңјеүҚзҡ„е…ЁзҗғеҢ–иҝӣзЁӢпјҒ
гҖҖгҖҖжҚ®и°ўеӨ©жҢҜиҜҙпјҢвҖңеҚҙдёҚзҹҘиҺ«иЁҖдҪңе“Ғзҡ„еӨ–иҜ‘дәӢе®һжӯЈеҘҪдёҺд»–жүҖи°Ҳзҡ„вҖҳеҝ е®һвҖҷиҜҙзӣёеҺ»з”ҡиҝңгҖӮиӢұиҜ‘иҖ…и‘ӣжө©ж–ҮеңЁзҝ»иҜ‘ж—¶жҒ°жҒ°дёҚжҳҜвҖҳйҖҗеӯ—гҖҒйҖҗеҸҘгҖҒйҖҗж®өвҖҷең°зҝ»иҜ‘пјҢиҖҢжҳҜвҖҳиҝһиҜ‘еёҰж”№вҖҷең°зҝ»иҜ‘зҡ„гҖӮд»–еңЁзҝ»иҜ‘иҺ«иЁҖзҡ„е°ҸиҜҙгҖҠеӨ©е Ӯи’ңиӢ”д№ӢжӯҢгҖӢж—¶з”ҡиҮіжҠҠеҺҹдҪңзҡ„з»“е°ҫж”№жҲҗдәҶзӣёеҸҚзҡ„з»“еұҖгҖӮ然иҖҢдәӢе®һиЎЁжҳҺпјҢи‘ӣжө©ж–Үзҡ„зҝ»иҜ‘жҳҜжҲҗеҠҹзҡ„гҖӮвҖқжҳҜд»Җд№ҲдәӢе®һиЎЁжҳҺпјҹжҳҜиҺ«иЁҖеҫ—еҘ–пјҹ
гҖҖгҖҖйҮ‘еІійң–еңЁжё…еҚҺи®ІгҖҠйҖ»иҫ‘еӯҰгҖӢпјҢ第дёҖиҜҫе°ұдёҫиҝҮиҝҷж ·дёҖдҫӢпјҢвҖңеҰӮжһңеӨ©дёӢйӣЁпјҢеҲҷең°дёҠж№ҝвҖқдёәзңҹпјҢвҖңеҰӮжһңең°дёҠж№ҝпјҢеҲҷеӨ©дёӢйӣЁвҖқжңӘеҝ…зңҹгҖӮд»ҘиҺ«иЁҖеҫ—еҘ–жқҘиҜҒжҳҺи‘ӣжө©ж–ҮеңЁзҝ»иҜ‘дёӯж”№еҶҷз»“еұҖпјҢжҚ®иҺ«иЁҖиҮӘе·ұиҜҙиҝҳеўһж·»дәҶжҖ§жҸҸеҶҷпјҢвҖңжҳҜжҲҗеҠҹзҡ„вҖқпјҢжңӘеҝ…зңҹгҖӮеӣ дёәиҺ«иЁҖе°ҸиҜҙеӨ–иҜ‘еҫҲеӨҡпјҢиҜ‘иҖ…дёҚйғҪжҳҜи‘ӣжө©ж–ҮпјҢдёҚйғҪж”№еҶҷгҖҒдёҚйғҪеўһж·»жҖ§жҸҸеҶҷгҖӮи°ўеӨ©жҢҜжҳҜиҜҙи‘ӣжө©ж–Үж”№еҫ—еҘҪпјҢиҝҳжҳҜиҜҙи°Ғж”№йғҪеҘҪпјҢдёҚж”№дёҚеҘҪпјҢдёҚж”№пјҢиҺ«иЁҖе°ұеҫ—дёҚдёҠеҘ–пјҢиҝҷе°ұжҳҜ规еҫӢпјҹдёҚпјҢи°Ғеҫ—еҘ–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规еҫӢпјҒ
гҖҖгҖҖд»–иҜҙпјҢвҖңжңүдәәжӣҫеҜ№иҺ«иЁҖдҪңе“ҒеӨ–иҜ‘зҡ„иҝҷз§ҚвҖҳиҝһиҜ‘еёҰж”№вҖҷиҜ‘жі•йўҮжңүеҫ®иҜҚпјҢиҙЁз–‘вҖҳйӮЈиҝҳжҳҜиҺ«иЁҖзҡ„дҪңе“Ғд№ҲпјҹвҖҷеҜ№жӯӨжҲ‘жғіжҸҗдёҖдёӢжһ—зәҫзҡ„зҝ»иҜ‘пјҢеҜ№дәҺжһ—иҜ‘дҪңе“ҒжҳҜдёҚжҳҜеӨ–еӣҪж–ҮеӯҰдҪңе“ҒжҒҗжҖ•дёҚдјҡжңүдәәиЎЁзӨәжҖҖз–‘еҗ§пјҹиҝҷйҮҢе…¶е®һзүөж¶үеҲ°дёҖдёӘж°‘ж—ҸжҺҘеҸ—еӨ–жқҘж–ҮеҢ–гҖҒж–ҮеӯҰзҡ„规еҫӢй—®йўҳпјҡе®ғйңҖиҰҒдёҖдёӘжҺҘеҸ—иҝҮзЁӢгҖӮжҲ‘们дёҚиҰҒеҝҳдәҶпјҢдёӯеӣҪиҜ»иҖ…д»ҺиҜ»жһ—зәҫзҡ„гҖҠеқ—иӮүдҪҷз”ҹиҝ°гҖӢеҲ°иҜ»д»ҠеӨ©зҡ„гҖҠеӨ§еҚ«В·з§‘жіўиҸІе°”гҖӢд№ғиҮівҖҳзӢ„жӣҙж–Ҝе…ЁйӣҶвҖҷпјҢиҠұдәҶдёҖзҷҫеӨҡе№ҙзҡ„ж—¶й—ҙгҖӮвҖқ
гҖҖгҖҖиҝҳжҳҜдёҖдёӘдёҚи¶ідёәи®ӯзҡ„жһ—иҜ‘пјҢдёҚжҮӮеӨ–ж–Үзҡ„вҖңзҝ»иҜ‘вҖқжҳҫ然дёҚжҳҜзңҹжӯЈзҡ„зҝ»иҜ‘гҖӮеҸҚеҜ№зҝ»иҜ‘еӯҰз ”з©¶зҝ»иҜ‘规еҫӢзҡ„и°ўеӨ©жҢҜпјҢеұ…然д»Ҙжһ—иҜ‘дёәдҫӢи°Ҳд»Җд№Ҳж–ҮеӯҰ规еҫӢгҖӮи°ўеӨ©жҢҜз ”з©¶иҝҮжһ—иҜ‘д№ҲпјҹжҲ‘зӣёдҝЎжІЎжңүгҖӮжҚ®гҖҠдёӯеӣҪзҝ»иҜ‘иҫһе…ёгҖӢиҜҙпјҢжһ—иҜ‘вҖңзғӮиҜ‘гҖҒж”№иҜ‘гҖҒеўһиҜ‘гҖҒжјҸиҜ‘гҖҒиҜҜиҜ‘д№ӢеӨ„дёҚе°‘пјҢжһ—зәҫиҜ‘дәҶдёҚе°‘иҘҝж–№еҗҚи‘—пјҢдҪҶжӣҙиҜ‘дәҶдёҚе°‘иҘҝж–№дәҢдёүжөҒдҪңе“ҒгҖӮжһ—зәҫжҠҠдёҖдәӣдјҳз§Җеү§дҪңеҰӮиҺҺеЈ«жҜ”дәҡзҡ„Henry IVе’ҢHenry VIзӯүпјҢиҜ‘жҲҗдәҶи®°еҸҷдҪ“зҡ„ж–ҮиЁҖе°ҸиҜҙгҖҠдәЁеҲ©з¬¬еӣӣзәӘгҖӢе’ҢгҖҠдәЁеҲ©з¬¬е…ӯйҒ—дәӢгҖӢпјҢеўһеҠ дәҶи®ёеӨҡеҸҷдәӢгҖӮеҚҙеҲ жҺүдәҶи®ёеӨҡеҜ№иҜқгҖӮвҖҰвҖҰжңүж—¶з”ҡиҮіжҠҠдҪңиҖ…зҡ„еӣҪзұҚд№ҹеј„й”ҷдәҶвҖқгҖӮй’ұй’ҹд№ҰиҜ»иҺҺеЈ«жҜ”дәҡпјҢд№ҹжҳҜеҸӘиҜ»жһ—иҜ‘пјҢдёҚиҜ»еҺҹж–Үпјҹ
гҖҖгҖҖвҖңеҜ№дәҺжһ—иҜ‘дҪңе“ҒжҳҜдёҚжҳҜеӨ–еӣҪж–ҮеӯҰдҪңе“ҒжҒҗжҖ•дёҚдјҡжңүдәәиЎЁзӨәжҖҖз–‘еҗ§пјҹвҖқиҝҷеҸҘиҜқжң¬иә«е°ұжҲҗй—®йўҳгҖӮеҰӮжһңй—®зҡ„жҳҜжһ—иҜ‘жүҖвҖңиҜ‘вҖқжҳҜдёҚжҳҜеӨ–еӣҪж–ҮеӯҰдҪңе“ҒгҖӮжҲ‘еҸҜд»Ҙеӣһзӯ”пјҢвҖңжһ—иҜ‘вҖқж¶үеҸҠиӢұгҖҒжі•гҖҒдҝ„гҖҒж—ҘеӣӣеӣҪдҪңе“Ғ184йғЁпјҢж №жҚ®пјҢдёҚжҳҜеҺҹ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д»–дәәеҸЈиҝ°пјҢе……е…¶йҮҸд№ҹеҸӘиғҪз®—иҪ¬иҜ‘пјҢжҠҠеҸЈиҝ°иҖ…зҡ„еҸЈиҝ°пјҢиҪ¬иҜ‘жҲҗ他笔дёӢзҡ„ж–ҮиЁҖж–№еқ—жұүеӯ—гҖӮжҳҜиҪ¬иҜ‘еҠ ж”№еҶҷпјҢдёҚжҳҜзҝ»иҜ‘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зҝ»иҜ‘еӨ–еӣҪдҪңе“ҒгҖӮи°ўеӨ©жҢҜз”Ёжһ—иҜ‘д»ЈиЎЁж–ҮеӯҰзҝ»иҜ‘пјҢе°ұеңЁйҖ»иҫ‘дёҠиҝқеҸҚдәҶеҗҢдёҖеҫӢгҖӮд»ҘжҺЁеҜјдёҚеҮәвҖңзҝ»иҜ‘жҖ»жҳҜеҰӮдҪ•еҰӮдҪ•вҖқзҡ„еӯӨдҫӢдёәиҜҒпјҢдҪңеҮәе…Ёз§°иӮҜе®ҡеҲӨж–ӯпјҢеҲҷиҝқеҸҚдәҶзҗҶз”ұе……и¶іеҫӢгҖӮдёҖиҙҜйј“еҗ№вҖңжӯЈжҳҜж–ҮеӯҰзҝ»иҜ‘зҡ„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пјҢжүҚеҰӮдҪ•еҰӮдҪ•вҖқпјҢеҸҲдёҚж•ўзқҒзңјзһҺиҜҙвҖңеҠӣжұӮеҝ е®һзҡ„иҜ‘дҪңеҸҚеҖ’дёҚеҲ©дәҺж–ҮеӯҰжқ°дҪңзҡ„дј ж’ӯе’ҢжҺҘеҸ—вҖқпјҢеҸҲиҝқеҸҚдәҶжҺ’дёӯеҫӢгҖӮ
гҖҖгҖҖи°ўеӨ©жҢҜе®Ғж„ҝйқўеҜ№зҺ°е®һи§ҶиҖҢдёҚи§Ғ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вҖңдёӯеӣҪиҜ»иҖ…д»ҺиҜ»жһ—зәҫзҡ„гҖҠеқ—иӮүдҪҷз”ҹиҝ°гҖӢеҲ°иҜ»д»ҠеӨ©зҡ„гҖҠеӨ§еҚ«В·з§‘жіўиҸІе°”гҖӢд№ғиҮівҖҳзӢ„жӣҙж–Ҝе…ЁйӣҶвҖҷпјҢиҠұдәҶдёҖзҷҫеӨҡе№ҙзҡ„ж—¶й—ҙвҖқпјҹе°ұеӣ дёәвҖңжһ—иҜ‘вҖқжҳҜеҚҒи¶ізҡ„вҖң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вҖқпјҢдёҚжҳҜзҝ»иҜ‘пјҢиҖҢдё”иҝҳеҸҜиғҪжҳҜеҸӣйҖҶзҡ„еҸӣйҖҶгҖӮиҮідәҺе…ЁйӣҶпјҢжӣҙдёҚиғҪиҜҙжҳҺд»Җд№ҲпјҢжңүдәӣеӨ–еӣҪдҪң家д№ҹи®ё500е№ҙд№ҹжңӘеҝ…дјҡжңүд»–зҡ„дёӯиҜ‘жң¬е…ЁйӣҶпјҢеҺҹеӣ еҗ„жңүдёҚеҗҢгҖӮдҪ зҹҘйҒ“зӢ„йҮ‘жЈ®д»ҺгҖҠиҜ—еҲҠгҖӢеҸ‘иЎЁжұҹжһ«зҡ„иҜ‘иҜ—пјҢз»ҷеҘ№зҡ„姓еҗҚе®ҡиҜ‘дёәиүҫзұіиҺүВ·зӢ„йҮ‘жЈ®пјҢеҲ°еҘ№еҸ—еҲ°дёӯеӣҪе№ҝеӨ§иҜ»иҖ…е’ҢеӯҰиҖ…зҡ„ж¬ўиҝҺгҖҒеӯҰд№ гҖҒз ”з©¶пјҢз”ЁдәҶеҮ е№ҙпјҹ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зӢ„йҮ‘жЈ®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жҳҜдёҖеӨңжҲҗеҗҚгҖӮдёәд»Җд№ҲпјҢеӣ дёәиҜ‘иҖ…иҝҪжұӮеҪўзҘһе…јеӨҮзҡ„еҝ е®һгҖӮе…¬и®ӨжңҖеҘҪзҡ„иҜ‘жң¬пјҢиў«еј•з”ЁгҖҒиў«з ”з©¶гҖҒиў«жҜ”иҫғгҖҒиў«дёҚеҗҢеҮәзүҲзӨҫеҮәдәҶеҸҲеҮәгҖҒиў«еүҪзӘғзҡ„пјҢиҝҳжҳҜ30е№ҙеүҚйӮЈдёӘжұҹиҜ‘жң¬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пјҢеӣ дёәеҝ е®һеәҰиҫҫеҲ°98%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зӢ„йҮ‘жЈ®пјҢеҚҙеҫҲеҸҜиғҪжҳҜеҶҚиҝҮ500е№ҙд№ҹжңӘеҝ…дјҡжңүеҪўзҘһе…јеӨҮдёӯиҜ‘жң¬е…ЁйӣҶзҡ„еӨ–еӣҪжқ°еҮәеҘіиҜ—дәәпјҢиҮӘжңүзӢ¬зү№еҺҹеӣ гҖӮ
гҖҖгҖҖеҰӮжһңжңӘз»ҸдҪңиҖ…жҺҲжқғпјҢиҜ‘иҖ…еңЁзҝ»иҜ‘дёӯж•…ж„ҸвҖңеҲӣйҖ жҖ§еҸӣйҖҶвҖқпјҢ第дёҖпјҢиҝқжі•пјҢдҫөзҠҜдәҶдҪңиҖ…зҡ„и‘—дҪңжқғгҖӮ第дәҢпјҢжҢӮзҫҠеӨҙеҚ–зӢ—иӮүпјҢд»ҘеҺҹдҪңиҖ…зҡ„姓еҗҚдёәе№ҢеӯҗеҮәе”®иҮӘе·ұзҡ„вҖңеҸӣйҖҶвҖқпјҢдҫөзҠҜ姓еҗҚжқғпјҢеҚұе®іж¶Ҳиҙ№иҖ…жқғзӣҠпјҢиҖҢдё”дёҚйҒ“еҫ·гҖӮ第дёүпјҢеңЁзҗҶи®әе’Ңе®һи·өдёӨж–№йқўиҙҘеқҸжҲ‘еӣҪж–ҮеӯҰзҝ»иҜ‘дәӢдёҡгҖӮ
|
| |
| |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