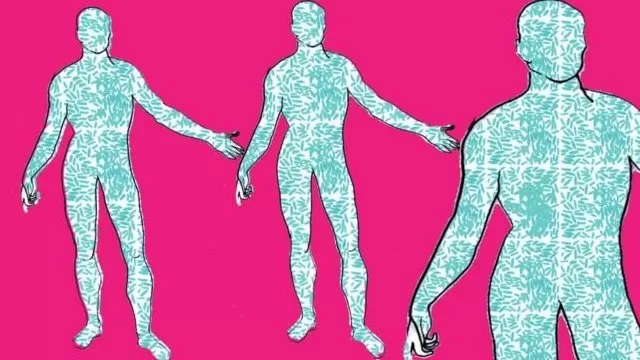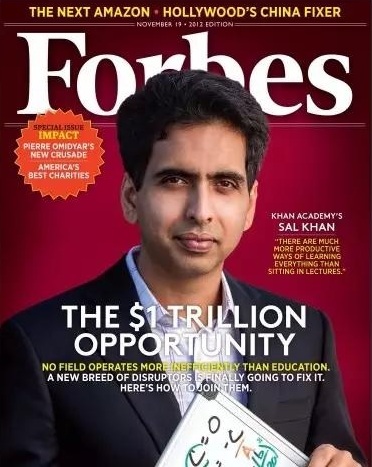еӯҷдёӯеұұ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дёҖдәӢпјҢиҜҘжҖҺд№ҲиҜ„д»·пјҹ | 2016-09-04 20:11:31 (иў«йҳ…иҜ» 1468 ж¬Ў) |  | | еӣҫзүҮдёҠпјҡ1890е№ҙд»Ј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дёҺж—Ҙжң¬еҸӢдәәеҗҲеҪұгҖӮ
еӣҫзүҮдёӯпјҡзҫҺеӣҪ移民еұҖжЎЈжЎҲеҶ…1904е№ҙеӯҷдёӯеұұиў«зҫҺеӣҪ移民еұҖжӢҳз•ҷгҖӮ
еӣҫзүҮдёӢпјҡе®Ӣж•ҷд»ҒгҖӮ1900е№ҙд»ЈпјҢе®Ӣд№ғвҖңдёӯеӣҪд№ғжұүдәәд№ӢдёӯеӣҪвҖқзҡ„зғӯзғҲжӢҘи¶ёгҖӮ
зҹӯеҸІи®° и…ҫи®ҜеҺҶеҸІ и°Ңж—ӯеҪ¬ 2016-09-02 00:13
[ж‘ҳиҰҒ]з»јиҖҢиЁҖд№ӢпјҢеңЁ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дёҖз”ҹеҪ“дёӯпјҢ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иҝҷ件дәӢжғ…зҡ„е…·дҪ“ж¶өд№үпјҢжҳҜйҡҸзқҖе…¶дёӘдәәжҖқжғізҡ„иҝӣеҢ–пјҢеңЁдёҚж–ӯеҸҳеҢ–зҡ„гҖӮ
еңЁ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дёҖз”ҹеҪ“дёӯпјҢ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дәӢжғ…жҜ”еҗ‘ж—Ҙжң¬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дёҖдәӢпјҢеңЁд»ҠеӨ©жӣҙиғҪеј•иө·дәүи®®пјҢз”ҡиҮіеҜ№е…¶дәәж јдә§з”ҹйў иҰҶжҖ§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ж•…иҖҢпјҢеңЁеӯҷдёӯеұұиҜһиҫ°150е‘Ёе№ҙд№Ӣйҷ…пјҢеҫҲжңүеҝ…иҰҒжҠҠиҝҷ件дәӢжғ…и®Іжё…жҘҡгҖӮ
еӨ§йҷҶеӯҰжңҜз•ҢиҮӘ90е№ҙд»Јд»ҘжқҘпјҢеҜ№еӯҷдёӯеұұ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дёҖдәӢе·ІдёҚеҶҚеӣһйҒҝ
е…ідәҺеӯҷдёӯеұұдёәжҚўеҸ–ж—Ҙжң¬еҜ№дёӯеӣҪйқ©е‘Ҫзҡ„жҸҙеҠ©пјҢжӣҫдёҖеәҰдёҚжғң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пјҢеӨ§йҷҶеӯҰжңҜз•ҢиҮӘ90е№ҙд»Јд»ҘжқҘе·ІдёҚеҶҚеӣһйҒҝгҖӮеҰӮжқЁеӨ©зҹіиЁҖйҒ“пјҡвҖңиҜҡ然пјҢдёәдәҶдёӯеӣҪзҡ„зӢ¬з«Ӣе’ҢеҜҢејә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йһ иә¬е°ҪзҳҒең°еҘӢж–—дәҶдёҖз”ҹ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— еҸҜдәүиҫ©зҡ„дәӢе®һ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№ҹжӯЈжҳҜдёәдәҶиҝҷдёҖзӣ®зҡ„пјҢд»–еҸҲеңЁзӣёеҪ“й•ҝзҡ„ж—¶жңҹеҶ…пјҢеҮҶеӨҮе°Ҷж»ЎжҙІз§ҹи®©з»ҷж—Ҙжң¬пјҢиҝҷеә”иҜҘд№ҹжҳҜдәӢе®һгҖӮвҖқв‘ жқЁеҘҺжқҫд№ҹиҜҙпјҡвҖңе…ідәҺеӯҷдёӯеұұжӣҫиҜ•еӣҫз”Ёз§ҹи®©дёӯеӣҪж»Ўе·һең°еҢәжқғзӣҠжҲ–жҸҗдҫӣе…¶е®ғзү№жқғзҡ„еҠһжі•пјҢжқҘжҚўеҸ–ж—Ҙжң¬еҶӣйҳҖжҲ–иҙўйҳҖжҸҙеҠ©дёӯеӣҪйқ©е‘Ҫзҡ„жғ…еҶөпјҢи®ёеӨҡе№ҙеүҚж—Ҙжң¬еӯҰиҖ…е°ұе…ҲеҗҺж’°ж–ҮеҠ д»ҘжҠ«йңІгҖӮеҜ№дәҺиҝҷдёҖиҜҙжі•пјҢд№ жғҜдәҺдёәе°ҠиҖ…и®ізҡ„дёҖдәӣеҸ°ж№ҫеӯҰиҖ…еҪ“е№ҙиҮӘ然жӢ’д№Ӣе”ҜжҒҗдёҚеҸҠдәҶгҖӮеҘҮжҖӘзҡ„жҳҜпјҢ并жңӘе°ҶеӯҷдёӯеұұеҘүиӢҘзҘһжҳҺзҡ„еӨ§йҷҶеӯҰиҖ…пјҢеҫҲеӨҡдәәеҜ№жӯӨд№ҹе§Ӣз»ҲжҠұд»ҘжҖҖз–‘з”ҡиҮіеҗҰи®Өзҡ„жҖҒеәҰгҖӮ然иҖҢпјҢйҡҸзқҖ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еҸІж–ҷиў«жҠ«йңІеҮәжқҘпјҢдёҚдҝЎдёҚи°ҲеҲ°еә•жҳҜдёҚжҲҗдәҶгҖӮвҖқв‘Ў
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д№ӢиҜҙпјҢеҜ№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еҪўиұЎпјҢйҖ жҲҗдәҶе·ЁеӨ§дјӨе®ігҖӮе°Ҫз®ЎеӯҰжңҜз•ҢеҜ№жӯӨеӨҡжҢҒвҖң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вҖқзҡ„жҖҒеәҰпјҢеҰӮдҝһиҫӣж·іж•ҷжҺҲи®ӨдёәпјҢеӯҷж°ҸжӯӨзұ»иЁҖиЎҢпјҢд№ғжҳҜеҹәдәҺвҖңйқ©е‘Ҫзҡ„зҹӯжңҹеҲ©зӣҠвҖқиҖҢйҮҮеҸ–зҡ„дёҖз§ҚвҖңжҡӮж—¶зүәзүІйғЁеҲҶеӣҪ家жқғзӣҠвҖқзҡ„зӯ–з•ҘжүӢж®өпјӣжқЁеҘҺжқҫж•ҷжҺҲд№ҹи®ӨдёәпјҢвҖңжҲ‘д»¬ж— и®әеҰӮдҪ•дёҚеә”еҪ“жӢҝжҲ‘们д»ҠеӨ©еҜ№еӣҪ家еҸҠе…¶дё»жқғйўҶеңҹд№Ӣзұ»зҡ„и§ӮеҝөпјҢжқҘиҜ„еҲӨеҺҶеҸІгҖӮвҖҰвҖҰжҲ‘们д№ҹдёҚеә”еҪ“жҠҠзҲұеӣҪдёҺжҡӮж—¶зҡ„еҰҘеҚҸгҖҒйҖҖи®©е’ҢжҡӮж—¶зүәзүІйғЁеҲҶеӣҪ家жқғзӣҠзҡ„еӨ–дәӨиЎҢдёәз®ҖеҚ•ең°еҜ№з«Ӣиө·жқҘпјҢж–Ҙд№ӢдёәдёҚзҲұеӣҪгҖӮеҺҶеҸІйңҖиҰҒеҲҶжһҗпјҢжӣҙйңҖиҰҒзҗҶи§ЈгҖӮвҖқвҖҰвҖҰдҪҶиҝҷз§Қи§ЈиҜ»пјҢдјје°ҡдёҚи¶ід»Ҙе®Ңе…Ёи§ЈйҮҠеӯҷзҡ„иЎҢдёәвҖ”вҖ”еӣ дёәеӯҷзҡ„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пјҢеңЁеүҚжңҹе°ҡеёҰжңүвҖңеүІи®©вҖқжҖ§иҙЁгҖӮ
1911е№ҙд№ӢеүҚпјҢ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еёҰжңүеүІи®©жҖ§иҙЁпјӣ1911е№ҙд№ӢеҗҺпјҢиҪ¬еҸҳдёәд»Ҙдҝқжңүж»ЎжҙІдё»жқғдёәеүҚжҸҗзҡ„з§ҹеҖҹгҖҒ委жүҳ
еңЁ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дёҖдәӢдёҠ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з«ӢеңәпјҢеӨ§иҮҙеҸҜд»Ҙ1911е№ҙиҫӣдәҘйқ©е‘ҪдёәеҲҶз•ҢзәҝпјҢеҢәеҲҶдёәеүҚеҗҺдёӨдёӘдёҚеҗҢзҡ„йҳ¶ж®өгҖӮеңЁеүҚдёҖйҳ¶ж®өпјҢеӯҷзҡ„ж„Ҹи§ҒеёҰжңүвҖңеүІи®©вҖқжҖ§иҙЁпјӣеҗҺдёҖйҳ¶ж®өеҲҷ收缩дёәвҖңз§ҹеҖҹвҖқгҖҒвҖң委жүҳвҖқжҖ§иҙЁгҖӮ
жҚ®ж—Ҙж–№иө„ж–ҷи®°иҪҪпјҢ1898е№ҙ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жӣҫеҜ№еҶ…з”°иүҜе№іиЁҖеҸҠпјҡвҖңеҗҫдәәд№Ӣзӣ®зҡ„еңЁдәҺзҒӯж»Ўе…ҙжұүпјҢйқ©е‘ҪжҲҗеҠҹд№Ӣж—¶пјҢеҚідҪҝд»ҘиҜёеҰӮж»ЎгҖҒи’ҷгҖҒиҘҝдјҜеҲ©дәҡд№Ӣең°жӮүдёҺж—Ҙжң¬пјҢеҪ“дәҰж— дёҚеҸҜгҖӮвҖқ1900е№ҙжғ е·һиө·д№үеүҚпјҢеӯҷжӣҫи®ҝй—®ж—Ҙжң¬еҰҮеҘіз•Ңи‘—еҗҚдәәеЈ«дёӢз”°жӯҢеӯҗпјҢиҜ·жұӮе…¶еҚҸеҠ©зӯ№жҺӘеҶӣиҙ№пјҢдёӢз”°з§°пјҡвҖңйқ©е‘ҪжҲҗеҠҹеҗҺпјҢйЎ»е°Ҷж»ЎжҙІи®©дёҺж—Ҙжң¬гҖӮвҖқеӯҷзӯ”пјҡвҖңеҸҜд»ҘвҖқгҖӮж—Ҙдәәе°Ҹе·қе№іеҗүд№ҹз§°пјҡиҫӣдәҘеүҚпјҢвҖңеҪјеұЎеұЎеҗ‘жҲ‘иҫҲйҷҲиҝ°пјҡвҖҰвҖҰе…¶ең°еҺҹдёәж»ЎжҙІдәәд№Ӣеңҹең°пјҢеҜ№жҲ‘дёӯеӣҪжұүдәәжқҘиҜҙ并йқһз»қеҜ№еҝ…иҰҒгҖӮжҲ‘иҫҲйқ©е‘ҪеҰӮиғҪжҲҗеҠҹпјҢеҰӮж»ЎжҙІд№Ӣең°пјҢеҚідҪҝж»Ўи¶іж—Ҙжң¬д№ӢеёҢжңӣпјҢеҪ“дәҰж— еҰЁгҖӮвҖқ并жҠұжҖЁиҜҙпјҢиҫӣдәҘеҗҺ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зӯүйқ©е‘Ҫе…ҡе°ұе®Ңе…Ёеҝҳи®°дәҶеҪ“е№ҙиҜҙиҝҮзҡ„иҜқгҖӮв‘ўиҝҷдәӣиө„ж–ҷдёӯзҡ„вҖңжӮүдёҺвҖқгҖҒвҖң и®©дёҺвҖқгҖҒвҖң еҺҹдёәж»ЎжҙІдәәд№Ӣеңҹең°вҖқзӯүеӯ—ж ·пјҢйғҪйҖҸжјҸеҮәдәҶвҖңеүІи®©вҖқд№Ӣж„ҸгҖӮ
1912е№ҙпјҢж—ҘдәәжЈ®жҒӘд»ЈиЎЁжЎӮеӨӘйғҺгҖҒеұұеҺҝжңүжңӢзӯүдәәпјҢдёҺеӯҷдёӯеұұе°ұвҖңж»ЎжҙІеҮәи®©вҖқй—®йўҳз§ҳеҜҶжҺҘи§ҰгҖӮеҜҶи°Ҳз»“жһңпјҢжҚ®жЈ®жҒӘд№Ӣз§ҳеҜҶжұҮжҠҘпјҢвҖңеӯҷе·ІеҗҢж„Ҹз§ҹеҖҹж»ЎжҙІпјҢж—Ҙжң¬иӢҘиғҪдёәйҳІжӯўйқ©е‘Ҫд№ӢзҰ»ж•ЈпјҢеңЁжұүеҶ¶иҗҚе…¬еҸёдә”зҷҫдёҮж—Ҙе…ғд№ӢеӨ–еҶҚиҝ…йҖҹжҸҗдҫӣдёҖеҚғдёҮж—Ҙе…ғеҖҹж¬ҫпјҢе°ҶдёӯжӯўдёҺиўҒдё–еҮҜд№Ӣи®®е’ҢпјҢеӯҷжң¬дәәжҲ–й»„е…ҙеҪ“иөҙж—Ҙжң¬и®ўз«Ӣе…ідәҺж»ЎжҙІд№Ӣз§ҳеҜҶеҘ‘зәҰгҖӮвҖқв‘Ј1913е№ҙеҲқпјҢеӯҷи®ҝй—®ж—Ҙжң¬пјҢжҚ®еұұз”°зәҜдёүйғҺеӣһеҝҶпјҢжЎӮеӨӘйғҺжӣҫеҗ‘еӯҷиҜҙиө·ж—Ҙжң¬дәәеҸЈеўһеҠ пјҢйҷӨдәҶеҗ‘ж»ЎжҙІеҸ‘еұ•еҲ«ж— д»–жі•пјҢиҜўй—®еӯҷиғҪеҗҰд»Ҙе…ұеҗҢзҡ„еҠӣйҮҸдҪҝж»ЎжҙІжҲҗдёәд№җеңҹпјҢеӯҷиЎЁзӨәеҗҢж„ҸвҖ”вҖ”зЁҚж—©дёҖдәӣж—¶еҖҷпјҢеӯҷеңЁеӣҪеҶ…еҜ№жҠҘз•ҢеҸ‘иЎЁи®ІиҜқж—¶пјҢеҲҷжңүвҖңж»ЎжҙІд№Ӣй“Ғи·ҜпјҢе…ЁеҪ’ж—Ҙдҝ„д№ӢжүӢпјҢвҖҰвҖҰи·ҜжқғдёҖеӨұпјҢдё»жқғйўҶеңҹпјҢеҝ…дёҺдҝұе°ҪпјҢжӯӨеӨ§еҸҜдёәеҜ’еҝғвҖқд№ӢиҫһгҖӮв‘Ө1915е№ҙпјҢеӯҷдёҺж—Ҙжң¬йҷҶеҶӣеҸӮи°Ӣй•ҝдёҠеҺҹеӢҮдҪңеҜҶи°ҲпјҢжӣҫе…ҒиҜәвҖңеҸҜд»Ҙж»ЎжҙІдҪңдёәж—Ҙжң¬зҡ„зү№ж®Ҡең°еҢәпјҢжүҝи®Өж—Ҙжң¬з§»ж°‘е’ҢејҖжӢ“зҡ„дјҳе…ҲжқғвҖқпјҢеҗҢж—¶еҸҲејәи°ғвҖңдёңдёүзңҒжҳҜдёӯеӣҪйўҶеңҹпјҢдё»жқғд»ҚеұһдәҺдёӯеӣҪвҖқгҖӮв‘Ҙ1917е№ҙпјҢжІідёҠжё…йҖ и®ҝе№ҝдёңеҶӣж”ҝеәңпјҢеӯҷжӣҫиЎЁзӨәпјҢиӢҘеҫ—еҲ°ж—Ҙжң¬ж–№йқўзҡ„жӯҰеҷЁгҖҒиҙ·ж¬ҫжҸҙеҠ©пјҢеҲҷеҸҜе°Ҷж»ЎжҙІвҖң委жүҳж—Ҙжң¬з®ЎзҗҶвҖқгҖӮв‘Ұд»ҘдёҠиҝҷдәӣжқҗж–ҷпјҢеқҮеҸҜжҳҫзӨәеӯҷеңЁиҫӣдәҘеҗҺпјҢ已然ж”ҫејғдәҶвҖңеүІ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зҡ„жғіжі•пјҢиҖҢиҪ¬дёәеңЁдҝқжңүдё»жқғзҡ„еүҚжҸҗдёӢвҖңз§ҹ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гҖҒвҖң委жүҳз®ЎзҗҶвҖқгҖӮ
1890е№ҙд»Ј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е’ҢжўҒеҗҜи¶…гҖҒи°ӯе—ЈеҗҢзӯүпјҢдҝұд»Ҙдј з»ҹзҡ„вҖңеҚҺеӨ·д№ӢиҫЁвҖқжқҘзңӢеҫ…жё…е»·е’Ңиҫ№з–Ҷең°еҢә
дёҠиҝ°иҪ¬еҸҳпјҢиҮӘ然дёҺжё…еёқйҖҠдҪҚгҖҒж°‘еӣҪйЎәеҲ©з»§жүҝжё…жңқзүҲеӣҫжңүе…ігҖӮдҪҶ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еӣ зҙ пјҢд№ғжҳҜеӯҷдёӯеұұ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и§Ӯеҝөзҡ„е·ЁеӨ§еҸҳеҢ–гҖӮ
еңЁ1890е№ҙд»Ј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йқ©е‘ҪиҖ…еҰӮеӯҷдёӯеұұпјҢиҝҳжҳҜвҖңж”№иүҜжҙҫвҖқеҰӮеә·жңүдёәгҖҒжўҒеҗҜи¶…пјҢе…¶жҖқжғідёҺзңјз•ҢйғҪиҝҳжІЎжңүиғҪеӨҹи¶…еҮәдј з»ҹзҡ„вҖңеҚҺеӨ·д№ӢиҫЁвҖқ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дёҚдҪҶеӯҷдёӯеұұжӣҫй«ҳе‘ј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еҸЈеҸ·вҖ”вҖ”1894е№ҙпјҢеӯҷж°ҸеңЁжӘҖйҰҷеұұеҲӣз«Ӣе…ҙдёӯдјҡпјҢе®ЈиӘ“вҖңй©ұйҷӨйһ‘иҷҸпјҢжҒўеӨҚдёӯеҚҺвҖқпјҢеә·гҖҒжўҒзӯүдәәд№ҹиө°еңЁ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иҝҗеҠЁзҡ„еүҚеҲ—вҖ”вҖ”жўҒеҗҜи¶…еңЁж№–еҚ—ж—¶еҠЎеӯҰе ӮпјҢдёҺе”җжүҚеёёиҫҲеҒ·еҚ°гҖҠжҳҺеӨ·еҫ…и®ҝеҪ•гҖӢгҖҒгҖҠжү¬е·һеҚҒж—Ҙи®°гҖӢзӯүеҸҚжё…д№ҰзұҚпјҢж·»еҠ жү№зӮ№жЎҲиҜӯпјҢз§ҳеҜҶж•ЈеҸ‘пјӣз”ҡиҮіеҲ©з”ЁгҖҠж№ҳжҠҘгҖӢ公然дёәгҖҠжҳҺеӨ·еҫ…и®ҝеҪ•гҖӢжү“е№ҝе‘Ҡпјӣи°ӯе—ЈеҗҢеңЁз»ҷд№ғеёҲ欧йҳідёӯ鹄зҡ„д№ҰдҝЎдёӯпјҢвҖң公然иҜҙж»Ўдәәи§ҶдёӯеӣҪдёәеӮҘжқҘд№Ӣзү©пјҢж— жүҖзҲұжғңвҖқпјҢдё”з§ҳеҜҶж•ЈеёғгҖҠеӨ§д№үи§үиҝ·еҪ•гҖӢгҖҒгҖҠй“ҒеҮҪеҝғеҸІгҖӢзӯүеҸҚжё…зҰҒд№ҰгҖӮеә·жңүдёәеҲҷж•ҷеҜјеә·й—ЁејҹеӯҗвҖңжіЁж„ҸеӨ§еҗҢеӣҪпјҢеӢҝжіЁж„ҸеӨ§жөҠеӣҪгҖӮвҖҰвҖҰеӨ§жөҠеӣҪеҝ…е°ҶеӨ§д№ұпјҢдёәдәәз“ңеҲҶпјҢзӢ¬еӨ«д№Ӣ家дә§дҪ•и¶іжғңпјҒвҖқеӣ иҖҢиў«еҫЎеҸІеј№еҠҫвҖңдҝқдёӯеӣҪдёҚдҝқеӨ§жё…вҖқвҖҰвҖҰ⑧
еӣ еҗҢе…·дј з»ҹвҖңеҚҺеӨ·д№ӢиҫЁвҖқзҗҶеҝөдёӢзҡ„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ж„ҸиҜҶпјҢеҪ“1898е№ҙеӯҷдёӯеұұеҗ‘еҶ…з”°иүҜе№іиЁҖеҸҠвҖңд»ҘиҜёеҰӮж»ЎгҖҒи’ҷгҖҒиҘҝдјҜеҲ©дәҡд№Ӣең°жӮүдёҺж—Ҙжң¬пјҢеҪ“дәҰж— дёҚеҸҜвҖқж—¶пјҢеә·жңүдёәгҖҒи°ӯе—ЈеҗҢзӯүдәәд№ҹжңүзұ»дјјзҡ„и§ӮзӮ№гҖӮеҰӮ1898е№ҙпјҢжңқе»·йҮҚиҮЈеӯҷ家йјҗиҙЁй—®еә·жңүдёәзҡ„ж–°ж”ҝжһ„жғівҖңдёҮз«Ҝ并иө·вҖқпјҢз»Ҹиҙ№е°ҶеҰӮдҪ•зӯ№жҺӘж—¶пјҢеә·еӣһзӯ”пјҡвҖңж— иҷ‘пјҢиӢұеҗүеҲ©еһӮж¶ҺиҘҝи—ҸиҖҢдёҚиғҪйҒҪеҫ—пјҢжңқе»·жһңиӮҜејғжӯӨиҚ’иҝңең°пјҢеҸҜеҫ—е–„д»·дҫӣж–°ж”ҝз”ЁпјҢдёҚйҡҫд№ҹгҖӮвҖқвҖңд»Ҙе…ЁеӣҪзҹҝдҪңжҠөпјҢиӢұзҫҺеҝ…д№җд»»д№ӢпјҢе…¶жңүдёҚиғҪпјҢеҲҷ鬻иҫ№еӨ–ж— з”Ёд№Ӣең°пјҢеҠЎеңЁзӯ№еҫ—жӯӨе·Ёж¬ҫпјҢд»Ҙз«Ӣе…ЁеұҖгҖӮвҖқ并еңЁиҝӣе‘Ҳз»ҷе…үз»ӘзҡҮеёқзҡ„гҖҠж—Ҙжң¬еҸҳж”ҝиҖғгҖӢдёҖд№ҰдёӯпјҢжҳҺзЎ®е»әи®®е…үз»ӘеҚ–жҺүвҖңиҫ№иҝңд№ӢиҚ’ең°вҖқпјҢжқҘдёәеҸҳжі•зӯ№жҺӘиҙ№з”ЁпјҢвҖңд»Ҙжҳ“йҮ‘й’ұиҖҢе…ҙеҶ…еҲ©вҖқгҖӮв‘Ё и°ӯе—ЈеҗҢд№ҹеңЁдёҺеҘҪеҸӢиҙқе…ғеҫҒзҡ„д№ҰдҝЎеҫҖжқҘдёӯпјҢдё»еј еҸҳеҚ–еӨ–и’ҷеҸӨгҖҒж–°з–ҶгҖҒиҘҝи—ҸгҖҒйқ’жө·пјҡвҖңи®ЎеҶ…еӨ–и’ҷеҸӨгҖҒж–°з–ҶгҖҒиҘҝи—ҸгҖҒйқ’жө·дёҚдёӢдәҢеҚғдёҮж–№йҮҢпјҢжҜҸж–№йҮҢеҫ—д»·дә”еҚҒдёӨпјҢе·ІдёҚдёӢеҚҒдёҮдёҮгҖӮйҷӨеҒҝиө”ж¬ҫеӨ–пјҢжүҖдҪҷе°ҡеӨҡпјҢеҸҜдҫӣеҸҳжі•д№Ӣз”ЁзҹЈгҖӮвҖқв‘©
жҳҫ然пјҢе’ҢеӯҷдёӯеұұдёҖж ·пјҢеә·жңүдёәгҖҒжўҒеҗҜи¶…гҖҒи°ӯе—ЈеҗҢзӯүпјҢеңЁ1898е№ҙеүҚеҗҺпјҢдҝұе°ҡж— еҸ‘з«ҜдәҺиҘҝж–№зҡ„иҝ‘д»ЈйўҶеңҹдё»жқғж„ҸиҜҶпјҢиҖҢд»Қд»Ҙдј з»ҹзҡ„вҖңеҚҺеӨ·д№ӢиҫЁвҖқжқҘзңӢеҫ…иҫ№з–Ҷең°еҢәгҖӮдёҚеҗҢзҡ„жҳҜпјҢеӯҷдҪңдёәйҖ еҸҚиҖ…пјҢеҸҜд»Ҙж— жүҖйЎҫеҝҢең°и®Ёи®әвҖңж»ЎжҙІвҖқпјӣеә·жўҒи°ӯзӯүеҶ…жҖҖ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жҖқжғіпјҢеӨ–иө°жңқе»·и·ҜзәҝпјҢиЁҖиҫһд№Ӣй—ҙеҜ№жё…е»·зҡ„вҖңйҫҷе…ҙд№Ӣең°вҖқдёҚеҫ—дёҚжңүжүҖеӣһйҒҝгҖӮ
1900е№ҙд»ЈпјҢеңЁйҮҺзҹҘиҜҶз•Ңеј•е…ҘиҘҝж–№еёҰз§Қж—Ҹдё»д№үиүІеҪ©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пјҢеңЁжҺ’ж»ЎжҖқжҪ®д№ӢдёӢ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жӣҫдё»еј вҖңдёӯеӣҪе»әеӣҪеңЁй•ҝеҹҺд»ҘеҶ…вҖқ
1900е№ҙд»ЈпјҢеңЁйҮҺ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пјҲж— и®әдё»еј йқ©е‘ҪжҠ‘жҲ–ж”№иүҜпјүеҗёж”¶дәҶиҘҝж–№еёҰжңүз§Қж—Ҹдё»д№үиүІеҪ©зҡ„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пјҢжӣҫжҺҖиө·дёҖеңә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ж•‘дёӯеӣҪвҖқзҡ„е·ЁеӨ§жҖқжҪ®гҖӮе…¶ејҖз«Ҝд№ғжҳҜ1902е№ҙжўҒеҗҜи¶…жүҖж’°еҶҷзҡ„гҖҠж–°еҸІеӯҰгҖӢгҖӮжўҒеңЁж–Үз« дёӯжҳҺзЎ®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жҸҗеҖ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пјҢд№ғжҳҜвҖңдҪҝжҲ‘еӣӣдёҮдёҮеҗҢиғһејәз«ӢдәҺжӯӨдјҳиғңеҠЈиҙҘд№Ӣдё–з•ҢвҖқзҡ„еҝ…йЎ»жүӢж®өгҖӮ1903е№ҙпјҢйқ©е‘Ҫе…ҡдәәдё»жҢҒзҡ„гҖҠжөҷжұҹжҪ®гҖӢжқӮеҝ—пјҢд№ҹеӨ§еЈ°з–ҫе‘јпјҡеҰӮжһңвҖңеҶҚдёҚд»Ҙ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жҸҗеҖЎдәҺеҗҫдёӯеӣҪпјҢеҲҷеҗҫдёӯеӣҪд№ғзңҹдәЎзҹЈпјҒвҖқ
иҝҷиӮЎжҖқжҪ®пјҢжһҒеӨ§ең°жҝҖеҸ‘дәҶеӣҪдәәзҡ„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ж„ҸиҜҶгҖӮжҢүжўҒеҗҜи¶…зӯүдәәзҡ„йҖ»иҫ‘пјҢиҘҝж–№еӣҪ家д№ӢжүҖд»ҘејәеӨ§пјҢд№ғжҳҜеӣ дёәе®ғ们жҳҜвҖңж°‘ж—ҸеӣҪ家вҖқпјӣдёӯеӣҪиҰҒејәеӨ§пјҢд№ҹйЎ»иҪ¬еһӢдёәж°‘ж—ҸеӣҪ家пјӣиҪ¬еһӢзҡ„еҪ“еҠЎд№ӢжҖҘпјҢеҲҷжҳҜд»ҘвҖңеҸІз•Ңйқ©е‘ҪвҖқ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жқҘжҝҖеҸ‘еӣҪдәәзҡ„вҖңж°‘ж—Ҹж„ҸиҜҶвҖқгҖӮеңЁиҝҷеңәж–ҮеҢ–йқ©ж–°иҝҗеҠЁдёӯпјҢзҹҘиҜҶз•ҢйҮҚжһ„еҺҶеҸІпјҢйҖ еҮәдәҶдёҖжқЎиҮӘй»„еёқиҖҢдёӢпјҢз”ұеІійЈһгҖҒж–ҮеӨ©зҘҘгҖҒеҸІеҸҜжі•гҖҒйғ‘жҲҗеҠҹгҖҒжҙӘз§Җе…ЁзӯүеҺҶеҸІдәәзү©з»„жҲҗзҡ„вҖңж°‘ж—ҸиӢұйӣ„вҖқи°ұзі»гҖӮеңЁиҝҷжқЎи°ұзі»дёӯпјҢй»„еёқжҺ’иҡ©е°ӨгҖҒеІійЈһжҠ—йҮ‘гҖҒж–ҮеӨ©зҘҘжҠ—е…ғгҖҒеҸІйғ‘жҙӘжҠ—жё…вҖҰвҖҰж— дёҚеҲҮеҗҲеҪ“дёӢ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д№Ӣж„ҸгҖӮжўҒеҗҜи¶…з”ҡиҮіеҶҷдҝЎз»ҷеә·жңүдёәпјҢжҳҺзЎ®иЎЁзӨәиҮӘе·ұдёҚиғҪйҒөд»Һеә·зҡ„еҠқиҜ«пјҢжҳҜдёҖе®ҡиҰҒ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зҡ„пјҢеӣ дёәвҖңжүҖд»Ҙе”Өиө·ж°‘ж—ҸзІҫзҘһиҖ…пјҢеҠҝдёҚеҫ—дёҚж”»ж»ЎжҙІгҖӮж—Ҙжң¬д»Ҙ讨幕дёәжңҖйҖӮе®ңд№Ӣдё»д№үпјҢдёӯеӣҪд»Ҙи®Ёж»ЎдёәжңҖйҖӮе®ңд№Ӣдё»д№үгҖӮвҖқпјҲ11пјүиҮідәҺйқ©е‘Ҫе…ҡдәәпјҢж— дёҚжҳҜ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дё»еј зҡ„жӢҘи¶ёпјҢеҰӮеңЁйҷ¶жҲҗз« зңӢжқҘпјҢвҖңеӯ°дёәдёӯеӣҪдәәпјҹжұүдәәз§ҚжҳҜд№ҹгҖӮ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иҖ…пјҢжұүдәәд№ӢеҺҶеҸІд№ҹгҖӮвҖқе®Ӣж•ҷд»Ғд№ҹе®Јз§°пјҡвҖңдёӯеӣҪиҖ…пјҢжұүж—Ҹд№ӢдёӯеӣҪд№ҹгҖӮвҖқ
еӯҷдёӯеұұеҪ“然д№ҹжҳҜиҝҷиӮЎ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ж•‘дёӯеӣҪвҖқжҖқжҪ®дёӯзҡ„дёҖе‘ҳпјҢз”ҡиҮі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еӯҷеҗҺжқҘвҖңдёүж°‘дё»д№үвҖқдёӯзҡ„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пјҢеҚіеҸ‘з«ҜдәҺиҝҷеңәжҖқжҪ®гҖӮ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еӯҷзҡ„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°ұжҳҜвҖңжҺ’ж»Ўдё»д№үвҖқгҖӮ еңЁгҖҠж°‘жҠҘгҖӢеҸ‘еҲҠиҜҚдёӯпјҢеӯҷиҜҙпјҡвҖңдёӯеӣҪд»ҘеҚғе№ҙдё“еҲ¶д№ӢжҜ’иҖҢдёҚи§ЈпјҢејӮз§Қж®Ӣд№ӢпјҢеӨ–йӮҰйҖјд№Ӣпј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гҖҒж°‘жқғдё»д№үж®ҶдёҚеҸҜд»ҘйЎ»иҮҫзј“вҖқпјӣеңЁдёҺеә·е…ҡи®әжҲҳж—¶пјҢеӯҷеҸҲе‘јжё…еёқдёәвҖңе®ўеёқвҖқпјҢиҙЈеӨҮеә·жңүдёәвҖңеҝҳжң¬жҖ§гҖҒжҳ§еӨ©иүҜгҖҒеҺ»еҗҢж—ҸиҖҢдәӢејӮз§ҚгҖҒиҲҚеҝ д№үиҖҢдёәжұүеҘёвҖқгҖҒвҖңдҝқејӮз§ҚиҖҢеҘҙдёӯеҚҺпјҢйқһзҲұеӣҪд№ҹпјҢе®һе®іеӣҪд№ҹвҖқпјҢ并ж„ҹж…ЁвҖңжұүдәәиҖ…пјҢеӨұеӣҪдәҢзҷҫдҪҷе№ҙвҖқпјҢеӣ вҖңиөҙеӘҡејӮз§ҚпјҢж•…дёӯеӣҪзҡ„ж–ҮжҳҺйҒӮиҮіиҗҪдәҺж—Ҙжң¬д№ӢеҗҺвҖқвҖҰвҖҰпјҲ12пјүвҖңејӮз§ҚвҖқдёӨеӯ—пјҢи¶іи§Ғе…¶вҖ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дёӯзҡ„вҖңз§Қ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иүІеҪ©гҖӮеңЁиҝҷж ·дёҖз§ҚжҖқжғізҡ„ж”Ҝй…ҚдёӢпјҢиҜҙеҮәвҖңе…¶ең°еҺҹдёәж»ЎжҙІдәәд№Ӣеңҹең°пјҢеҜ№жҲ‘дёӯеӣҪжұүдәәжқҘиҜҙ并йқһз»қеҜ№еҝ…иҰҒвҖқиҝҷж ·зҡ„иҜқпјҢжҳҜдёҖзӮ№йғҪдёҚеҘҮжҖӘзҡ„вҖ”вҖ”1906е№ҙпјҢеӯҷж°ҸжӣҫеҜ№ж—Ҙдәә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дёӯеӣҪйқ©е‘Ҫзӣ®зҡ„еңЁдәҺзҒӯж»Ўе…ҙжұүпјҢдёӯеӣҪе»әеӣҪеңЁй•ҝеҹҺд»ҘеҶ…гҖӮвҖқ
иҫӣдәҘе№ҙеүҚеҗҺпјҢжўҒеҗҜи¶…гҖҒ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и§ӮеҝөеқҮжңүжһҒеӨ§зҡ„иҝӣеҢ–пјҢдҝқжңүвҖңж»ЎжҙІдё»жқғвҖқжҲҗдёәеӯҷдёӯеұұдёҚеҸҜеҠЁж‘Үзҡ„дёҖжқЎеә•зәҝ
д»ҠдәәеҪ“然еҸҜд»ҘиҙЈеӨҮеӯҷзҡ„иҝҷз§ҚвҖңз§Қ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еӨӘиҝҮзӢӯйҡҳгҖӮдҪҶеҗҢж—¶д№ҹйЎ»зҹҘпјҢд»ҘжҝҖеҸ‘вҖңз§Қж—Ҹж„ҸиҜҶвҖқдёәж ёеҝғеҶ…е®№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пјҢеҪ“ж—¶е°ҡжҳҜе…Ёдәәзұ»зҡ„иҝ·жҖқгҖӮжўҒгҖҒеӯҷиҜёдәәе°Ҷе…¶еј•е…ҘдёӯеӣҪпјҢе®һжңүдёҺеҗҢж—¶д»ЈиҘҝж–№вҖңе…ҲиҝӣвҖқж–ҮжҳҺвҖңжҺҘиҪЁвҖқзҡ„ејәзғҲж„ҝжңӣеңЁе…¶дёӯгҖӮ
1905е№ҙпјҢи§ҒиҜҶжёҗж·ұзҡ„жўҒеҗҜи¶…пјҢејҖе§Ӣи„ұзҰ»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йҳөиҗҘпјҢдәҺгҖҠеҺҶеҸІдёҠдёӯеӣҪж°‘ж—Ҹд№Ӣи§ӮеҜҹгҖӢдёҖж–ҮдёӯпјҢйҰ–ж¬ЎжҸҗеҮәвҖң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вҖқдёҖиҜҚгҖӮжўҒи®ӨдёәпјҢ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д»ҺдёҖејҖе§Ӣе°ұдёҚжҳҜеҚ•дёҖзҡ„з§Қж—ҸпјҢиҖҢжҳҜеӨҡз§Қж—Ҹж··еҗҲиҖҢжҲҗгҖӮеӯҷдёӯеұұе…·дҪ“дҪ•ж—¶ж‘Ҷи„ұзӢӯйҡҳзҡ„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ж„ҸиҜҶпјҢе°ҡеҫ…иҖғиҜҒвҖ”вҖ”еӣ йқ©е‘Ҫе…ҡдәәд»Ҙ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дёәеҸ‘еҠЁж°‘дј—зҡ„йҮҚиҰҒе·Ҙе…·пјҢж•…еӯҷеңЁиҫӣдәҘеүҚд»ҺжңӘе…¬ејҖжү№иҜ„иҝҮвҖңжҺ’ж»ЎвҖқпјҢдҪҶ1912е№ҙе…ғж—ҰеҸ‘еёғзҡ„гҖҠдёҙж—¶еӨ§жҖ»з»ҹе®ЈиЁҖд№ҰгҖӢдёӯпјҢеӯҷж°Ҹзҡ„иҜҙжі•е·ІдёҺжўҒеҗҜи¶…зҡ„ж„Ҹи§ҒйўҮдёәзӣёиҝ‘пјҢеңЁеӯҷзңӢжқҘпјҢжүҖи°“ж°‘ж—Ҹз»ҹдёҖпјҢеҚіжҳҜвҖңеҗҲжұүгҖҒж»ЎгҖҒи’ҷгҖҒеӣһгҖҒи—ҸиҜёж—ҸдёәдёҖдәәвҖқгҖӮ
еҲ°1920е№ҙеүҚеҗҺ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ж°‘ж—Ҹи§ӮеҝөпјҢеҸҲжңүдёҖж¬Ўе·ЁеӨ§зҡ„еҸҳеҢ–гҖӮеӯҷжӣҫеҜ№еӣҪж°‘е…ҡдәәеҰӮжӯӨ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зҺ°еңЁиҜҙдә”ж—Ҹе…ұе’ҢпјҢе®һеңЁиҝҷдә”ж—Ҹзҡ„еҗҚиҜҚеҫҲдёҚеҲҮеҪ“гҖӮжҲ‘们еӣҪеҶ…дҪ•жӯўдә”ж—Ҹе‘ўпјҹжҲ‘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еә”иҜҘжҠҠжҲ‘们дёӯеӣҪжүҖжңүеҗ„ж°‘ж—ҸиһҚжҲҗдёҖдёӘ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(еҰӮзҫҺеӣҪпјҢжң¬жҳҜ欧жҙІи®ёеӨҡж°‘ж—ҸеҗҲиө·жқҘзҡ„пјҢзҺ°еңЁеҚҙеҸӘжҲҗдәҶзҫҺеӣҪдёҖдёӘж°‘ж—ҸпјҢдёәдё–з•ҢдёҠжңҖжңүе…үиҚЈзҡ„ж°‘ж—Ҹ)пјӣ并且иҰҒжҠҠ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йҖ жҲҗеҫҲж–ҮжҳҺзҡ„ж°‘ж—ҸпјҢ然еҗҺ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д№ғдёәе®ҢдәҶгҖӮвҖқпјҲ13пјүж»Ўж—Ҹж—ўеұһвҖң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вҖқдёӯдёҚеҸҜеҲҶеүІзҡ„дёҖд»ҪеӯҗпјҢеӯҷдёӯеұұиҮӘд№ҹдёҚеҶҚеҜ№ж—ҘиЁҖеҸҠвҖңеүІ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пјҢиҪ¬иҖҢеңЁе•Ҷи°ҲеҮәи®©вҖңж»ЎжҙІеҲ©жқғвҖқж—¶пјҢдёҖеҶҚејәи°ғе…¶дё»жқғдёҚе®№дҫөзҠҜдәҶгҖӮ
з»“иҜӯ
з»јиҖҢиЁҖд№ӢпјҢеңЁеӯҷдёӯеұұзҡ„дёҖз”ҹеҪ“дёӯпјҢ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иҝҷ件дәӢжғ…зҡ„е…·дҪ“ж¶өд№үпјҢжҳҜйҡҸзқҖе…¶дёӘдәәжҖқжғізҡ„иҝӣеҢ–пјҢеңЁдёҚж–ӯеҸҳеҢ–зҡ„гҖӮд»ҠдәәеңЁе®Ўи§ҶеӯҷжҳҜеҗҰвҖңзҲұеӣҪвҖқж—¶пјҢйЎ»дәҶи§ЈеӯҷжүҖеӨ„зҡ„ж—¶д»ЈпјҢд№ғжҳҜдёҖз§ҚеҚғе№ҙжңӘжңүд№ӢеӨ§еҸҳеұҖгҖӮеҜ№еӯҷиҖҢиЁҖпјҢвҖңзҲұеӣҪвҖқжҜӢеәёзҪ®з–‘пјҢдҪҶвҖңеӣҪвҖқ究з«ҹдёәдҪ•зү©пјҢеҚҙд»ҚжҳҜ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гҖӮд»ҺвҖңеҚҺеӨ·д№ӢиҫЁвҖқпјҢеҲ°вҖңз§Қ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пјҢеҶҚеҲ°вҖңдә”ж—Ҹе…ұе’ҢвҖқпјҢз»ҲиҮівҖң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вҖқпјҢвҖңеӣҪвҖқзҡ„ж¶өд№үеңЁеҸҳпјҢвҖңеҮә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зҡ„еә•зәҝд№ҹеңЁеҸҳгҖӮд»Ҡдәәеә”зҗҶи§Јиҝҷз§ҚвҖңеҸҳвҖқзҡ„дёҚжҳ“пјӣжҜ•з«ҹпјҢд»Ҡдәәжү№иҜ„еүҚдәәж—¶жүҖдҪҝз”Ёзҡ„з§Қз§Қи§Ӯеҝөе’ҢжҰӮеҝөпјҲеҰӮйўҶеңҹдё»жқғгҖҒ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пјүпјҢе…¶е®һд№ҹжҳҜеүҚдәәдёҚж–ӯж‘ёзҙўгҖҒзә й”ҷзҡ„вҖңеҸҳвҖқжүҖз•ҷдёӢзҡ„йҒ—дә§гҖӮ
жіЁйҮҠ
в‘ жқЁеӨ©зҹіпјҢгҖҠеӯҷдёӯеұұдёҺвҖңз§ҹ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й—®йўҳгҖӢпјҢгҖҠиҝ‘д»ЈеҸІз ”究гҖӢ1988е№ҙ第6жңҹгҖӮв‘ЎжқЁеҘҺжқҫпјҢгҖҠеӯҷдёӯеұұеҮәи®©ж»Ўи’ҷжқғзӣҠй—®йўҳзҡ„еҶҚжҺўи®ЁпјҡиҜ„жқҺеҗүеҘҺ<еӯҷдёӯеұұдёҺж—Ҙжң¬>пјӣдҝһиҫӣж·ігҖҲеӯҷдёӯеұұдёҺж—Ҙжң¬е…ізі»з ”究гҖүгҖӢпјҢгҖҠдёӯз ”йҷўиҝ‘еҸІжүҖйӣҶеҲҠгҖӢ第40жңҹгҖӮв‘ўжқЁеӨ©зҹіпјҢгҖҠеӯҷдёӯеұұдёҺвҖңз§ҹи®©ж»ЎжҙІвҖқй—®йўҳгҖӢпјҢгҖҠиҝ‘д»ЈеҸІз ”究гҖӢ1988е№ҙ第6жңҹгҖӮв‘Ји—Өдә•еҚҮдёүпјҢгҖҠвҖңеӯҷж–ҮдёҺж»ЎжҙІвҖқй—®йўҳгҖӢпјҢ收еҪ•дәҺгҖҠеӣҪеӨ–иҫӣдәҘйқ©е‘ҪеҸІз ”究еҠЁжҖҒВ·7гҖӢпјҢP07гҖӮв‘ӨеӯҷдёӯеұұпјҢгҖҠж¬Іи§ЈеҶіеӨ–дәӨй—®йўҳйЎ»еҸ–й—ЁжҲ·ејҖж”ҫдё»д№үгҖӢпјҢ1912/09/05гҖӮв‘ҘеӯҷдёӯеұұпјҢдёҺж—Ҙжң¬дёҠеҺҹеӢҮдҪңзҡ„и°ҲиҜқпјҲ1915е№ҙжң«жҲ–1916е№ҙеҲқпјүгҖӮ收еҪ•дәҺгҖҠеӯҷдёӯеұұйӣҶеӨ–йӣҶгҖӢпјҢP225-226гҖӮв‘Ұи—Өдә•еҚҮдёүпјҢгҖҠвҖңеӯҷж–ҮдёҺж»ЎжҙІвҖқй—®йўҳгҖӢпјҢ收еҪ•дәҺгҖҠеӣҪеӨ–иҫӣдәҘйқ©е‘ҪеҸІз ”究еҠЁжҖҒВ·7гҖӢпјҢP08гҖӮ⑧еҸҜеҸӮи§Ғпјҡй»„еҪ°еҒҘпјҢгҖҠжҲҠжҲҢеҸҳжі•еҸІз ”究пјҲдёҠеҶҢпјүгҖӢпјҢдёҠжө·д№Ұеә—еҮәзүҲзӨҫпјҢ2007пјҢP124-378гҖӮв‘ЁиҢ…жө·е»әпјҢгҖҠд»Һз”ІеҚҲеҲ°жҲҠжҲҢ еә·жңүдёәгҖҲжҲ‘еҸІгҖүйүҙжіЁгҖӢпјҢ з”ҹжҙ»В·иҜ»д№ҰВ·ж–°зҹҘдёүиҒ”д№Ұеә—пјҢ2009пјҢP348гҖӮв‘©и°ӯе—ЈеҗҢпјҢгҖҠжҠҘиҙқе…ғеҫҒгҖӢпјҢ收еҪ•дәҺгҖҠи°ӯе—ЈеҗҢйӣҶгҖӢпјҢеІійә“д№ҰзӨҫпјҢ2012пјҢP224гҖӮпјҲ11пјүжўҒеҗҜи¶…пјҢгҖҠе…үз»ӘдәҢеҚҒе…«е№ҙеҚҒжңҲдёҺеӨ«еӯҗеӨ§дәәд№ҰгҖӢпјҢ收еҪ•дәҺгҖҠжўҒеҗҜи¶…е№ҙи°ұгҖӢпјҢP157гҖӮпјҲ12пјүеҸӮи§ҒпјҡгҖҠ敬е‘ҠеҗҢд№Ўи®әйқ©е‘ҪдёҺдҝқзҡҮд№ӢеҲҶйҮҺд№ҰгҖӢпјҲ1903пјүпјҢгҖҠж”ҜйӮЈдҝқе…ЁеҲҶеүІеҗҲи®әгҖӢпјҲ1903пјүгҖҒгҖҠй©ідҝқзҡҮжҠҘгҖӢпјҲ1903пјүгҖҒгҖҠдёӯеӣҪеә”е»әи®ҫе…ұе’ҢеӣҪгҖӢпјҲ1905пјүгҖӮзӯүгҖӮпјҲ13пјүеӯҷдёӯеұұпјҢгҖҠдҝ®ж”№з« зЁӢд№ӢиҜҙжҳҺгҖӢпјҢ1920е№ҙ11жңҲ4ж—ҘеңЁдёҠжө·дёӯеӣҪеӣҪж°‘е…ҡжң¬йғЁдјҡи®®еёӯдёҠжј”и®ІгҖӮ |
| |
| |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