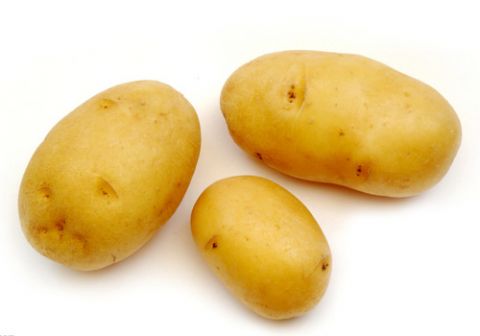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зҡ„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 | 2015-10-06 22:33:00 (иў«йҳ…иҜ» 853 ж¬Ў) |  | 2015-10-05 22:30
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зҡ„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
вҖ”вҖ”д»Ҙйқ’и’ҝзҙ иҺ·еҘ–еј•еҸ‘дәүи®әдәӢ件дёәдҫӢ
гҖҠ科еӯҰеӯҰз ”з©¶гҖӢ2015 Vol.33 (6): 810-814
ж‘ҳиҰҒеұ е‘Ұе‘Ұеӣ 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иҺ·еҫ—жӢүж–Ҝе…ӢеҢ»еӯҰеҘ–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еј•еҸ‘дәҶе…ідәҺ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е…ізі»зҡ„дәүи®әгҖӮжң¬ж–ҮеңЁйҳҗжҳҺйқ’и’ҝзҙ еӨ§еҚҸдҪңиғҢжҷҜеҸҠеҸ‘зҺ°иҝҮзЁӢзҡ„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еҲҶжһҗ并жҜ”иҫғдёӯеӣҪ科еӯҰжүҝи®Өе’ҢеҘ–еҠұдёӯвҖңйӣҶдҪ“дё»д№үвҖқ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дёҺзҫҺ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жіЁйҮҚзӢ¬еҲӣжҖ§е’ҢдёӘдәә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вҖңдёӘдәәдё»д№үвҖқ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пјҢжңҖеҗҺжң¬ж–Үи®Ёи®әдәҶеҰӮдҪ•еӨ„зҗҶ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зҡ„е…ізі»й—®йўҳпјҢжҢҮеҮәдёӘдәәеҜјеҗ‘зҡ„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дёҺ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еӣҪ家дә§жқғз»“жһ„пјҢйӣҶдҪ“еҜјеҗ‘зҡ„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дёҺе…¬е…ұдә§жқғз»“жһ„еҜҶеҲҮиҒ”зі»пјҢ并и®ӨдёәдёӨз§Қ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еҗ„жңүдјҳеҠЈпјҢеҰӮдҪ•еңЁеҲ¶еәҰи®ҫи®ЎдёӯжӣҙеҘҪең°еӨ„зҗҶ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йӣҶдҪ“дёҺдёӘдҪ“зҡ„е…ізі»д»Қ然жҳҜдёҖдёӘеҖјеҫ—з ”з©¶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
е…ій”®иҜҚйқ’и’ҝзҙ иҺ·еҘ–пјӣ科еӯҰеҘ–еҠұпјӣдёӘдәәпјӣйӣҶдҪ“пјӣ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пјӣе…¬е…ұдә§жқғ
еј•иЁҖ
2011е№ҙ9жңҲ12ж—ҘпјҢдёӯеӣҪ科еӯҰ家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еҫ—зҫҺеӣҪжңҖй«ҳ科еӯҰеҘ–вҖ”вҖ”жӢүж–Ҝе…ӢдёҙеәҠеҢ»еӯҰз ”з©¶еҘ–пјҲLaskerAwardsпјүгҖӮжӢүж–Ҝе…ӢеҘ–иў«иӘүдёәвҖңзҫҺеӣҪиҜәиҙқе°”еҘ–вҖқгҖҒвҖңиҜәиҙқе°”зҡ„йЈҺеҗ‘ж ҮвҖқпјҢжһҒе…·д»ҪйҮҸдё”зҰ»иҜәиҙқе°”еҫҲиҝ‘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жӯӨеҘ–дҪҝеҫ—дёӯеӣҪдәәзү№еҲ«жҳҜдёӯеӣҪ科еӯҰ家еҫ—д»ҘжҝҖеҠұ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еј•еҸ‘дәҶдёҖдәӣдәүи®әгҖӮдәүи®әеҶ…е®№еҢ…жӢ¬пјҢ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зҺ°жҳҜдёӘдәәзҡ„жҲҗеҠҹиҝҳжҳҜйӣҶдҪ“жҷәж…§зҡ„з»“жҷ¶пјҢеҘ–йЎ№йўҒз»ҷеұ е‘Ұе‘ҰдёӘдәәжҳҜеҗҰеҗҲзҗҶпјӣ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зҺ°дёәд»Җд№Ҳ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еңЁдёӯеӣҪеҫ—еҲ°и¶іеӨҹзҡ„жүҝи®ӨпјҲжІЎжңүиҺ·еҫ—иҝҮдёҖдёӘдёҖзӯүеҘ–пјүзӯүпјҢдј—иҜҙзә·зәӯпјҢжҢҒжӯЈйқўдёҺеҸҚйқўи§ӮзӮ№иҖ…зҡҶдј—гҖӮеүҚдёҖз§Қдәүи®әиө·жәҗдәҺйқ’и’ҝзҙ еҸ‘зҺ°зү№ж®Ҡзҡ„еҶӣж°‘иҒ”еҗҲзҡ„еӨ§еҚҸдҪңгҖҒеӨ§йЎ№зӣ®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пјҢе®һиҙЁдёҠжҳҜеҗҲдҪңйЎ№зӣ®дёӯ科еӯҰжүҝи®Өе’ҢиҚЈиӘүеҰӮдҪ•еҗ‘йӣҶдҪ“е’ҢдёӘдәәеҲҶй…Қ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еңЁдёҖе®ҡзЁӢеәҰдёҠеҸҚжҳ дәҶдёӯеӣҪе’ҢзҫҺ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зҡ„е·®ејӮвҖ”вҖ”дёӯеӣҪејәи°ғ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пјҢзҫҺеӣҪејәи°ғ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пјҢеҚідёӯеӣҪе…іжіЁзҡ„йҮҚзӮ№жҳҜвҖңйӣҶдҪ“вҖқеҜ№з§‘еӯҰжҲҗе°ұ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еҖҫеҗ‘дәҺзӘҒеҮәдёӘдәәеңЁйӣҶдҪ“зҡ„еҗҲдҪңдёӯеҸ‘жҢҘдҪңз”ЁпјҢзҫҺеӣҪејәи°ғвҖңдёӘдәәвҖқ科еӯҰеҸ‘зҺ°зҡ„дјҳе…ҲжқғпјҢжӣҙејәи°ғеҜ№дёӘдәәзҡ„жүҝи®Өе’ҢеҘ–еҠұгҖӮеҪ“дёӨз§Қдҫ§йҮҚжңүжүҖдёҚеҗҢзҡ„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еҸ‘з”ҹвҖңдәӨйӣҶвҖқж—¶пјҢеҸ—дёӯ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еҪұе“Қзҡ„дёҚе°‘дёӯеӣҪж°‘дј—ж— жі•жҺҘеҸ—зҫҺ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зҡ„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еҸ–еҗ‘пјҢдәҺжҳҜдә§з”ҹдәҶз–‘й—®е’Ңдәүи®әпјҢз–‘й—®зҡ„дә§з”ҹд№ҹдёҺеҪ“ж—¶й«ҳеәҰйӣҶдёӯзҡ„и®ЎеҲ’科еӯҰж”ҝзӯ–жңүе…ігҖӮ
е…ідәҺдёӯеӣҪ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еҘ–еҠұдёҚи¶ій—®йўҳпјҢдёӯеӣҪ科еҚҸдё»еёӯйҹ©еҗҜеҫ·и®ӨдёәпјҢ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жҳҺд»…д»…з”ұдәҺйҡҫд»ҘзЎ®е®ҡжҲҗжһңеҪ’е®ҝпјҢиҖҢ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пјҲеңЁдёӯеӣҪпјүеҫ—еҲ°и¶іеӨҹзҡ„иЎЁеҪ°е’ҢеҘ–еҠұпјҢе…¶дёӯжҠҳе°„еҮәзҡ„дёҚе°‘й—®йўҳеҖјеҫ—жҲ‘们ж·ұжҖқвҖқ[1]гҖӮ
жң¬ж–Үе°Ҷд»Ҙ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еҘ–еј•еҸ‘дәүи®әдәӢ件дёәжЎҲдҫӢпјҢжҺўи®ЁеҰӮдҪ•зңӢеҫ…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зҡ„е…ізі»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ж–Үз« йҰ–е…ҲеҲҶжһҗ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дёҺиҝҮзЁӢпјҢиҝӣиҖҢеҲҶеҲ«и®Ёи®әдёӯеӣҪе’ҢзҫҺеӣҪ科еӯҰз•ҢеҰӮдҪ•еҜ№иҝҷдёҖйҮҚиҰҒеҸ‘зҺ°дәҲд»ҘеҘ–еҠұпјҢжңҖеҗҺжҜ”иҫғеҲҶжһҗдёӨз§ҚдёҚеҗҢзҡ„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еҸҠе…¶еӯҳеңЁ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
1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дёҺиҝҮзЁӢ
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зҺ°жәҗдәҺдёӯеӣҪ1966е№ҙејҖе§Ӣзӯ№еӨҮпјҢ1967е№ҙејҖе§ӢиҝҗдҪң并жҢҒз»ӯиҝ‘10е№ҙзҡ„з ”з©¶жҠ—з–ҹз–ҫиҚҜзү©зҡ„еӨ§еһӢйЎ№зӣ®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гҖӮиҜҘд»»еҠЎжҳҜжҜӣжіҪдёңдё»еёӯе’Ңе‘ЁжҒ©жқҘжҖ»зҗҶжҺҘеҸ—и¶ҠеҚ—зҡ„иҜ·жұӮпјҢеҗҢж—¶дёәдәҶи§ЈеҶідёӯеӣҪеҚ—ж–№зҡ„з–ҹз–ҫй—®йўҳиҖҢејҖеұ•зҡ„пјҢ他们еҪ“е№ҙжүҖеҒҡзҡ„жҢҮзӨәз§°пјҡвҖңжҠҠи§ЈеҶізғӯеёҰең°еҢәйғЁйҳҹйҒӯеҸ—з–ҹз–ҫдҫөе®іпјҢдёҘйҮҚеҪұе“ҚйғЁйҳҹжҲҳж–—еҠӣпјҢеҪұе“ҚеҶӣдәӢиЎҢеҠЁ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йЎ№зҙ§жҖҘжҸҙеӨ–гҖҒжҲҳеӨҮйҮҚиҰҒд»»еҠЎз«ӢйЎ№вҖқ[2]гҖӮ
дёӯеӣҪ科еӯҰжҠҖжңҜ委е‘ҳдјҡе’ҢжҖ»еҗҺеӢӨйғЁдәҺ1967е№ҙ5жңҲ23ж—ҘеңЁеҢ—дә¬йҘӯеә—еҸ¬ејҖдәҶжҠ—з–ҹиҚҜзү©з ”究全еӣҪеҚҸдҪңдјҡи®®пјҢи®Ёи®әзЎ®е®ҡдәҶйЎ№зӣ®дёүе№ҙз ”з©¶и§„еҲ’[2]гҖӮжңүе…ідёҡеҠЎйўҶеҜјйғЁй—Ёе’Ңд»ҺдәӢз–ҹз–ҫиҚҜзү©з ”究иҜ•еҲ¶гҖҒз”ҹдә§гҖҒзҺ°еңәйҳІжІ»е·ҘдҪңзҡ„37дёӘеҚ•дҪҚпјҢ88еҗҚд»ЈиЎЁеҸӮеҠ дәҶдјҡи®®[3]гҖӮеҮәдәҺеҶӣдәӢдҝқеҜҶ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дёҺдјҡи®®зӣёе…ізҡ„з ”з©¶е’ҢеҚ•дҪҚз®Җз§°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гҖҒвҖң523йўҶеҜје°Ҹз»„вҖқе’ҢвҖң523еҠһе…¬е®ӨвҖқзӯүгҖӮ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дёҖзӣҙиҝҗиЎҢеҲ°20дё–зәӘ7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пјҢиҝҷеңЁз§‘з ”з»Ҹиҙ№е’ҢиҜҫйўҳжһҒе°‘зҡ„вҖңж— дә§йҳ¶зә§ж–ҮеҢ–еӨ§йқ©е‘ҪвҖқж—¶жңҹ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зү№дҫӢ[4]гҖӮ
1969е№ҙпјҢж—¶д»»дёӯеҢ»з ”究йҷўдёӯиҚҜз ”з©¶жүҖе®һд№ з ”з©¶е‘ҳзҡ„еұ е‘Ұе‘ҰдҪңдёәдёӯиҚҜз ”з©¶е°Ҹз»„з»„й•ҝеҠ е…Ҙ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пјҢиҜҘз»„зҡ„д»»еҠЎжҳҜвҖңд»ҺдёӯиҚҜдёӯеҜ»жүҫжҠ—з–ҹиҚҜвҖқпјҢе°Ҹз»„жҲҗе‘ҳиҝҳжңүдҪҷдәҡзәІгҖҒйЎҫеӣҪжҳҺгҖҒй’ҹиЈ•е®№зӯүгҖӮеұ е‘Ұе‘ҰжңҖеҲқд»Ҙй»„дё№зӯүзҹҝзү©иҚҜеҸҠе…¶й…ҚдјҚдёәдёӯиҚҜе…іжіЁйҮҚзӮ№гҖӮдҪҷдәҡзәІзҡ„е…іжіЁйҮҚзӮ№жҳҜиғЎжӨ’пјҢеҜ№иғЎжӨ’зҡ„е®һйӘҢеӨұиҙҘеҗҺпјҲ1970е№ҙпјүпјҢд»–ејҖе§ӢеҸӮиҖғ1965е№ҙдёҠжө·дёӯеҢ»ж–ҮзҢ®з ”究йҰҶзј–еҶҷзҡ„гҖҠз–ҹз–ҫдё“иҫ‘гҖӢзӯӣйҖүиҚҜзү©пјҢе…ұзӯӣйҖүеҮә808дёӘж–№еүӮпјҢеҲҶжһҗеҗҺеҲ—еҮәд№ҢеӨҙгҖҒд№Ңжў…гҖҒйі–з”ІгҖҒйқ’и’ҝзӯүйҮҚзӮ№иҚҜзү©гҖӮд»–е’ҢйЎҫеӣҪжҳҺе°ҶйҖүдёӯзҡ„иҚҜзү©еҒҡжҲҗеҲ¶еүӮпјҢиҝӣиЎҢйј з–ҹжЁЎеһӢе®һйӘҢпјҢ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еҜ№йј з–ҹеҺҹиҷ«жӣҫеҮәзҺ°иҝҮ60%вҖ”вҖ”80%зҡ„жҠ‘еҲ¶зҺҮпјҢдҪҶж•ҲжһңдёҚеӨӘзЁіе®ҡгҖӮдҪҷдәҡзәІдёҖеәҰжҠҠжіЁж„ҸеҠӣйӣҶдёӯеңЁеҜ№йј з–ҹеҺҹиҷ«жҠ‘еҲ¶зҺҮжӣҫй«ҳиҫҫ90%зҡ„йӣ„й»„дёҠпјҢеҗҺеӣ йӣ„й»„еҠ зғӯеҲ°дёҖе®ҡжё©еәҰеҗҺдјҡж°§еҢ–дә§з”ҹеү§жҜ’жҲҗеҲҶиҖҢж”ҫејғпјҢеҸҲе°ҶжіЁж„ҸеҠӣйӣҶдёӯеңЁжҠ‘еҲ¶зҺҮ第дәҢзҡ„йқ’и’ҝдёҠпјҢ并е°Ҷе…¶з»“жһңе‘ҠзҹҘз»„й•ҝеұ е‘Ұе‘ҰгҖӮ
1970е№ҙеә•пјҢдҪҷдәҡзәІиў«и°ғзҰ»523д»»еҠЎз»„гҖӮ1971е№ҙдёӢеҚҠе№ҙ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д»ҺдёңжҷӢи‘ӣжҙӘгҖҠиӮҳеҗҺеӨҮжҖҘж–№гҖӢдёӯе°Ҷйқ’и’ҝвҖңз»һжұҒвҖқз”ЁиҚҜзҡ„з»ҸйӘҢпјҢеҚівҖңйқ’и’ҝдёҖжҸЎпјҢд»Ҙж°ҙдёҖеҚҮжёҚпјҢз»һе…¶жұҒпјҢе°ҪжңҚд№ӢвҖқдёӯжӮҹеҸҠйқ’и’ҝзҡ„жңүж•ҲжҲҗеҲҶеҸҜиғҪеҝҢй«ҳжё©жҲ–й…¶и§ЈпјҢж”№з”Ёд№ҷйҶҡжҸҗеҸ–пјҢз»ҸеҸҚеӨҚе®һйӘҢпјҢдәҺ1971е№ҙ10жңҲ4ж—ҘеҲҶзҰ»иҺ·еҫ—зј–еҸ·191зҡ„йқ’и’ҝдёӯжҖ§жҸҗеҸ–зү©ж ·е“ҒпјҢжҳҫзӨәеҜ№йј з–ҹеҺҹиҷ«е…·жңү100%зҡ„жҠ‘еҲ¶зҺҮ[5]гҖӮе…¶еҗҺпјҢй’ҹиЈ•е®№жҲҗеҠҹиҺ·еҫ—дәҶжҠ—з–ҹжңүж•ҲеҚ•дҪ“вҖ”вҖ”жҷ¶дҪ“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в…ЎвҖқпјҲеҗҺз§°йқ’и’ҝзҙ пјүпјҢе®Ңе…ЁзЎ®е®ҡдәҶжҠ—з–ҹеҲҶеӯҗ[4]гҖӮ
е…ідәҺжҳҜеҗҰдҪҷдәҡзәІе’ҢйЎҫеӣҪжҳҺ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дҪҷдәҡзәІеҜ№дәҺ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дәҺеұ е‘Ұе‘Ұзҡ„дәүи®ә[6]пјҢеҸҠеұ гҖҒдҪҷгҖҒйЎҫгҖҒй’ҹеңЁйқ’и’ҝзҙ дёӯзҡ„иҙЎзҢ®иҜ„д»·й—®йўҳпјҢйҘ¶жҜ…з»ҸиҝҮз ”з©¶еҸІж–ҷи®ӨдёәвҖңдёӯеҢ»з ”究йҷўйҰ–е…ҲжҳҜдҪҷдәҡзәІе’ҢйЎҫеӣҪжҳҺ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ҡ„жҠ—з–ҹдҪңз”ЁпјҢе…¶еҗҺеұ е‘Ұе‘ҰеңЁд»–们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зЎ®е®ҡе…¶дҪңз”ЁпјҢ并еӣ дёәз”Ёд№ҷйҶҡеҫ—еҲ°жӣҙй«ҳз–—ж•ҲгҖӮеұ е‘Ұе‘Ұзҡ„иҝҷдёҖе·ҘдҪңеҸҠе…¶е°Ҹз»„зҡ„й’ҹиЈ•е®№жҸҗеҸ–йқ’и’ҝзҙ пјҢдёӨйЎ№еҠ иө·жқҘдҪҝеұ е‘Ұе‘Ұзҡ„иҙЎзҢ®зӘҒеҮәвҖқ[7]гҖӮ
2 дёӯеӣҪ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вҖқжүҝи®Өе’ҢеҘ–еҠұзҡ„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
еұ е‘Ұе‘Ұе°Ҹз»„1971е№ҙ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пјҢ1972е№ҙеңЁеҚ—дә¬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дјҡи®®дёҠжҠҘе‘ҠиҝҷйЎ№еҸ‘зҺ°пјҢ1977е№ҙе°Ҷз ”з©¶з»“жһңд»Ҙ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еҚҸеҠ©з»„вҖқзҡ„йӣҶдҪ“笔еҗҚеҸ‘表第дёҖзҜҮдёӯж–Үи®әж–ҮпјҢ1982е№ҙз”Ё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еҸҠе…¶иЎҚз”ҹжҠ—з–ҹиҚҜеҗҲдҪңз»„вҖқзҡ„йӣҶдҪ“笔еҗҚеҸ‘иЎЁиӢұж–Үи®әж–ҮгҖӮ
йқ’и’ҝзҙ еңЁдёӯеӣҪзҡ„иҺ·еҘ–жғ…еҶөжҳҜпјҢ1978е№ҙйЎ№зӣ®иҺ·е…ЁеӣҪ科еӯҰеӨ§дјҡвҖңеӣҪ家йҮҚеӨ§з§‘жҠҖжҲҗжһңеҘ–вҖқпјҢ1979е№ҙ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еӣҪ家科委еӣҪ家еҸ‘жҳҺеҘ–дәҢзӯүеҘ–пјҲеҘ–йҮ‘5000е…ғпјүпјҢ1984е№ҙйқ’и’ҝзҙ иў«дёӯеҚҺеҢ»еӯҰдјҡзӯүиҜ„дёәвҖңе»әеӣҪ35е№ҙд»ҘжқҘ20йЎ№йҮҚеӨ§еҢ»иҚҜ科жҠҖжҲҗжһңвҖқд№ӢдёҖпјҢ1992е№ҙеҸҢж°ўйқ’и’ҝзҙ иў«еӣҪ家科委зӯүиҜ„дёәвҖңе…ЁеӣҪеҚҒеӨ§з§‘жҠҖжҲҗе°ұеҘ–вҖқпјҢ1996е№ҙйқ’и’ҝзҙ иҺ·жұӮжҳҜ科еӯҰеҹәйҮ‘дјҡвҖңжқ°еҮә科жҠҖжҲҗе°ұйӣҶдҪ“еҘ–вҖқпјҢ1997е№ҙеҸҢж°ўйқ’и’ҝзҙ иў«еҚ«з”ҹйғЁиҜ„дёәвҖңж–°дёӯеӣҪеҚҒеӨ§еҚ«з”ҹжҲҗе°ұвҖқпјҢ2009е№ҙ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з¬¬дёүеұҠдёӯеӣҪдёӯеҢ»з§‘еӯҰйҷўе”җж°ҸдёӯиҚҜеҸ‘еұ•еҘ–пјҢ2011е№ҙпјҲеұ иҺ·жӢүж–Ҝе…ӢеҘ–д№ӢеҗҺпјү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дёӯеӣҪдёӯеҢ»з§‘еӯҰйҷўжқ°еҮәиҙЎзҢ®еҘ–пјҢйқ’и’ҝзҙ з ”з©¶еӣўйҳҹиҺ·еҘ–йҮ‘100дёҮе…ғдәәж°‘еёҒгҖӮ
1996е№ҙпјҢйқ’и’ҝзҙ жүҖиҺ·еҫ—зҡ„жұӮжҳҜ科жҠҖеҹәйҮ‘дјҡвҖңжқ°еҮә科жҠҖжҲҗе°ұйӣҶдҪ“еҘ–вҖқ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дёҺе…¶д»–д№қдәәдёҖиө·иҺ·еҘ–пјҢеҚҒдәәеқҮеҲҶдёҖзҷҫдёҮе…ғеҘ–йҮ‘гҖӮиҺ·еҘ–йҖҡзҹҘжқҘеҮҪз§°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еҘ–зҡ„зҗҶз”ұжҳҜвҖңеңЁйҮҮз”Ёд№ҷйҶҡжҸҗеҸ–йқ’и’ҝжҠ—з–ҹжңүж•ҲйғЁеҲҶзҡ„з ”з©¶е·ҘдҪңдёӯпјҢжүҖеҸ–еҫ—зҡ„ж–°зҡ„жҲҗе°ұпјҢеҜ№зӨҫдјҡеҸҠдәәзұ»еҒҘеә·жңүе®һиҙЁзҡ„иҙЎзҢ®вҖқ[8]пјҢеҘ№еңЁжұӮжҳҜ科еӯҰеҹәйҮ‘дјҡзҪ‘йЎөзҡ„еҫ—еҘ–дәәеҗҚжҺ’еәҸдёӯпјҢдҪҚеұ…第дёғдҪҚгҖӮ
523д»»еҠЎжҳҜдёӯеӣҪдёҫеӣҪз§‘з ”гҖҒеҶӣж°‘еӨ§иҒ”еҗҲ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еҪ“ж—¶пјҢеҗ„еҚҸдҪңз»„з ”з©¶дәәе‘ҳеңЁд»»еҠЎдёҠеҲҶе·ҘеҗҲдҪңпјҢеңЁдё“дёҡдёҠеҸ–й•ҝиЎҘзҹӯпјҢеңЁжҠҖжңҜдёҠдә’зӣёдәӨжөҒпјҢеңЁи®ҫеӨҮдёҠдә’йҖҡжңүж— пјӣ523д»»еҠЎзҡ„еӨ§еҚҸдҪңд№ҹдҪҝеҫ—дёӯиҚҜжҺўзҙўд№Ӣи·Ҝдә§з”ҹпјҢдҪҝеҫ—дәәеҠӣеҸҠиҙўеҠӣиө„жәҗеҗ‘523йЎ№зӣ®еҖҫж–ңпјҢдҪҝеҫ—з§‘з ”зӘҒз ҙзҡ„ж—¶й—ҙзј©зҹӯпјӣйқ’и’ҝзҙ еҸ‘зҺ°еүҚпјҢе…¶д»–йЎ№зӣ®з»„жҲҗе‘ҳжүҖеҒҡзҡ„зҙҜз§ҜжҖ§зҡ„гҖҒиҜ•й”ҷе’ҢжҺўзҙўжҖ§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дёӯиҚҜе°Ҹз»„зҡ„е…¶д»–йҮҚиҰҒеҗҲдҪңеҚ•дҪҚеҰӮ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дёҠжө·жңүжңәжүҖгҖҒ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з”ҹзү©зү©зҗҶз ”з©¶жүҖзӯүжүҖеҒҡзҡ„иҙЎзҢ®йғҪдёҚе®№еҝҪи§Ҷе’ҢеҗҰи®ӨгҖӮеұ е‘Ұе‘Ұ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д№ӢеҗҺпјҢйҰ–е…ҲеңЁ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дјҡи®®дёҠе…¬ејҖйқ’и’ҝзҙ ж•°жҚ®иҖҢдёҚжҳҜд»ҘдёӘдәәеҗҚд№үеҸ‘иЎЁи®әж–ҮпјӣйЎ№зӣ®з»„д»ҘйӣҶдҪ“笔еҗҚеҸ‘иЎЁдёӯиӢұи®әж–ҮпјҢеҚійӣҶдҪ“еҲҶдә«зҹҘиҜҶдә§жқғпјӣйқ’и’ҝзҙ жүҖиҺ·еҘ–еҠұдёҚе°‘пјҢдёҚиҝҮеӨ§йғЁеҲҶдёәйӣҶдҪ“еҘ–йЎ№дё”д»ҺжңӘиҺ·еҫ—иҝҮеӣҪ家зә§еҲ«зҡ„дёҖзӯүеҘ–пјҢиҝҷдёҺжӢүж–Ҝе…ӢеҹәйҮ‘дјҡзҡ„еҒҡжі•еҪўжҲҗдәҶйІңжҳҺзҡ„еҜ№жҜ”пјҢжұӮжҳҜ科еӯҰеҹәйҮ‘дјҡдёәйқ’и’ҝзҙ йўҒеҸ‘жқ°еҮә科жҠҖжҲҗе°ұйӣҶдҪ“еҘ–пјҢеҚҒдәәеқҮеҲҶеҘ–йҮ‘зӯүз§Қз§Қз§‘з ”жҲҗжһңйӣҶдҪ“еҢ–зҡ„еҒҡжі•дҪҝеҫ—вҖңйӣҶдҪ“вҖқзҡ„дҪңз”Ёеҫ—д»ҘиӮҜе®ҡгҖҒејәи°ғгҖҒеҮёжҳҫпјҢз”ҡиҮіеӨёеӨ§пјҢ笔иҖ…жҠҠе®ғз§°дҪң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гҖӮдёӯеӣҪ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жҲҗжһңеҘ–еҠұдёҚеӨҹпјҢд№ҹдҪҝеҫ—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еҒҡеҮәйҮҚеӨ§иҙЎзҢ®зҡ„дёӘдәәе’ҢжҲҗжһңжң¬иә«иў«ж·№жІЎеңЁйӣҶдҪ“е’Ңе…¶е®ғзҡ„жҷ®йҖҡ科еӯҰжҲҗе°ұдёӯпјҢеҪ“然пјҢиҝҷжҳҜеҸҰдёҖдёӘеұӮйқў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
жӯЈеҰӮдёӯеӣҪ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Ҙ–еҠұ并жңӘе®Ңе…ЁеҝҪз•ҘеҜ№дёӘдәәзҡ„еҘ–еҠұдёҖж ·пјҢжұӮжҳҜ科жҠҖеҹәйҮ‘дјҡеңЁжҺҲеҘ–иҝҮзЁӢдёӯд№ҹ并жңӘе®Ңе…ЁеҝҪз•ҘйЎ№зӣ®з»„дёӯдёӘдҪ“科еӯҰ家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иҙЎзҢ®зҡ„е·®ејӮпјҢ他们еҜ№е·®еҲ«зҡ„еӨ„зҗҶеҚіпјҢеңЁжҺҲдәҲйӣҶдҪ“еҘ–е’ҢеҜ№иҺ·еҘ–дәәе№іеқҮеҲҶй…Қдёәж•°дёҚеӨҡзҡ„еҘ–йҮ‘зҡ„еүҚжҸҗдёӢпјҢиҜ„йҖүеҮәе…·жңүжңҖеӨ§иҙЎзҢ®зҡ„еҚҒдҪҚ科еӯҰ家пјҢжҢү照他们жүҖи®Өе®ҡ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иҝӣиЎҢжҺ’еәҸпјҢеҚіиҺ·еҘ–еҗҚеҚ•зҡ„зЎ®е®ҡдҪҝеҫ—е°ҸйғЁеҲҶдёӘдәәеңЁйӣҶдҪ“дёӯзӘҒеҮәпјҢиҺ·еҘ–дәәеҗҚеӯ—зҡ„жҺ’еәҸдҪҝеҫ—иҺ·еҘ–иҖ…зҡ„йҮҚиҰҒзЁӢеәҰеҫ—д»ҘеҢәеҲҶгҖӮеҜ№дёӘдәәе·®еҲ«зҡ„еӨ„зҗҶеҖјеҫ—е…іжіЁеҫ—жҳҜпјҢдёҺжӢүж–Ҝе…ӢеҘ–зҡ„еӨ§еҠӣйҰ–иӮҜдёҚеҗҢ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зҡ„иҺ·еҘ–зҗҶз”ұе’ҢжҺ’еҗҚ并没жңүеӨ„дәҺеҘ–еҠұзҡ„дёӯеҝғпјҢжҺ’еңЁз¬¬дёҖдҪҚзҡ„жҳҜи’ҝз”ІйҶҡзҡ„еҸ‘жҳҺиҖ…пјҢеҸҜи§ҒпјҢдёӘдәәеҲӣйҖ жҖ§зҡ„еӨ§е°Ҹ并йқһеҹәйҮ‘дјҡзҡ„жҺ’еҗҚдҫқжҚ®гҖӮ
ж №жҚ®йҘ¶жҜ…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е°Ҹз»„еңЁжІЎжңүеҸ‘иЎЁж–Үз« пјҢеҸ–еҫ—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ңЁдјҡи®®дёҠе…¬ејҖйқ’и’ҝзҙ еҸ‘зҺ°еҸҠе…¶ж•°жҚ®пјҢ且延иҝҹе…ӯе№ҙжүҚеҸ‘表第дёҖзҜҮдёӯж–Үж–Үз« зҡ„еҒҡжі•пјҢ并дёҚз¬ҰеҗҲзҺ°д»ЈдёӯеӨ–дҪңиҖ…е…ҲеҸ‘иЎЁи®әж–ҮеҶҚдёҺе…¶д»–дәәеҲҶдә«з ”究жҲҗжһңзҡ„常规科еӯҰе®һи·ө[4]гҖӮиҝҷеңЁдёҖе®ҡж„Ҹд№үдёҠжҳҜдёӯеӣҪ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и§ӮеҝөеҜ№з§‘еӯҰ家塑йҖ 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з»ҙжҠӨдёӘдәә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дёҺиҝҷж ·зҡ„и§ӮеҝөзӣёиҝқиғҢпјҢжҳҜвҖңдёҚеҗҲжі•вҖқ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еҸ—йҳ»зўҚзҡ„гҖӮдҫӢеҰӮ1996е№ҙ8жңҲ31ж—Ҙ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еңЁжұӮжҳҜ科еӯҰеҹәйҮ‘дјҡзҡ„йўҒеҘ–д»ӘејҸдёҠжҢү规е®ҡз®ҖеҚ•жұҮжҠҘдәҶйқ’и’ҝзҙ еҸҠеҸҢж°ў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з ”еҲ¶еҺҶзЁӢпјҢе°ұйҒӯеҲ°дәҶдёҖдәӣдәәзҡ„иҜҹз—…пјҢи®ӨдёәеҘ№зҡ„жҠҘе‘ҠеӨӘиҝҮеҮёжҳҫиҮӘе·ұзҡ„еңЁйқ’и’ҝзҙ еҸ‘зҺ°иҝҮзЁӢдёӯ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
е°Ҫз®Ў523д»»еҠЎжҳҜиҢғеӣҙйўҮе№ҝзҡ„еӨ§еҚҸдҪңпјҢжӯЈеҰӮдёҠж–ҮжүҖи®әеҸҠзҡ„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йҮҮз”Ёд№ҷйҶҡжҸҗеҸ–жі•еҜ№дәҺ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зҺ°жқҘиҜҙиҝҲеҮәдәҶе…ій”®жҖ§зҡ„гҖҒж ёеҝғзҡ„дёҖжӯҘгҖӮеҚідҪҝжҠӣеҚҙиҜ„еҘ–科еӯҰ家们зҡ„еҖҫеҗ‘е’Ңе…ҙи¶ЈпјҢеҘ№дёҚеҸҜжӣҝд»Јзҡ„зү№ж®ҠиҙЎзҢ®д№ҹдјҡиў«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зҡ„д»·еҖји§ӮеҸ–еҗ‘жүҖжЁЎзіҠеҢ–гҖӮ
3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вҖқзҫҺ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зҡ„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
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дәӢйҡ”40е№ҙеҗҺзҡ„2011е№ҙ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вҖңдёӘдәәвҖқиў«жҺҲдәҲдә«иӘүе…Ёзҗғзҡ„зҫҺеӣҪжӢүж–Ҝе…ӢдёҙеәҠеҢ»еӯҰеҘ–пјҢеҘ–еҠұеҘ№вҖңеҸ‘зҺ°дәҶйқ’и’ҝзҙ вҖ”вҖ”дёҖз§ҚжІ»з–—з–ҹз–ҫзҡ„иҚҜзү©пјҢжҢҪж•‘дәҶе…ЁзҗғгҖҒзү№еҲ«жҳҜеҸ‘еұ•дёӯеӣҪ家数зҷҫдёҮдәәзҡ„з”ҹе‘ҪвҖқгҖӮжӢүж–Ҝе…ӢеҹәйҮ‘дјҡзҪ‘з«ҷиҝҷж ·иҜ„д»·еҘ№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вҖңеұ е‘Ұе‘ҰејҖеҲӣжҖ§ең°еҸ‘зҺ°дәҶйқ’и’ҝзҙ пјҢејҖеҲӣдәҶз–ҹз–ҫжІ»з–—ж–°ж–№жі•пјҢдё–з•ҢеҮ зҷҫдёҮдәәеӣ жӯӨеҸ—зӣҠпјҢжңӘжқҘиҝҳдјҡжңүжӣҙеӨҡзҡ„дәә们е°ҶеҸ—зӣҠвҖқ[9]гҖӮзҫҺеӣҪеӣҪз«ӢеҚ«з”ҹз ”з©¶йҷўпјҲNIHпјүзҡ„зұіеӢ’В·и·Ҝжҳ“ж–ҜеңЁгҖҠз»ҶиғһгҖӢжқӮеҝ—дёҠж’°ж–Үи§ЈйҮҠжҺҲеҘ–дәҲеұ е‘Ұе‘Ұзҡ„зҗҶз”ұпјҢвҖңз»ҸиҝҮж·ұе…Ҙзҡ„и°ғжҹҘз ”з©¶пјҢжҲ‘们жҜ«ж— з–‘й—®ең°еҫ—еҮәз»“и®әпјҡдёӯеӣҪдёӯеҢ»з§‘еӯҰйҷўеҢ—дә¬дёӯиҚҜз ”з©¶жүҖзҡ„еұ е‘Ұе‘Ұж•ҷжҺҲжҳҜ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йҰ–иҰҒиҙЎзҢ®иҖ…гҖӮ1969е№ҙ1жңҲ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иў«д»»е‘ҪдёәеҢ—дә¬дёӯиҚҜз ”з©¶жүҖ523иҜҫйўҳз»„зҡ„з»„й•ҝпјҢйўҶеҜјеҜ№дј з»ҹдёӯеҢ»иҚҜж–ҮзҢ®е’Ңй…Қж–№зҡ„жҗңеҜ»дёҺж•ҙзҗҶгҖӮ1981е№ҙ10жңҲ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еңЁеҢ—дә¬д»ЈиЎЁ523йЎ№зӣ®йҰ–ж¬Ўеҗ‘еҲ°и®ҝзҡ„дё–з•ҢеҚ«з”ҹз»„з»Үз ”з©¶дәәе‘ҳжұҮжҠҘдәҶйқ’и’ҝзҙ жІ»з–—з–ҹз–ҫзҡ„жҲҗжһңвҖқ[10]гҖӮ
жҲ‘们еҸ‘зҺ°пјҢзҫҺеӣҪжӢүж–Ҝе…ӢеҹәйҮ‘дјҡдёҺдёӯеӣҪжұӮжҳҜ科жҠҖеҹәйҮ‘дјҡеҜ№еұ е‘Ұе‘ҰжҺҲеҘ–еңЁжҖ§иҙЁе’ҢзҗҶз”ұж–№йқўеӯҳеңЁжһҒеӨ§зҡ„е·®ејӮпјҢеңЁжҖ§иҙЁж–№йқўпјҢеүҚиҖ…жҳҜдёӘдәәеҘ–пјҢеҗҺиҖ…жҳҜеұ е‘Ұе‘ҰжҺ’еҗҚ第дёғдҪҚзҡ„йӣҶдҪ“еҘ–жҲ–е…¶д»–еҲҶйҮҸдёҚи¶ізҡ„еҘ–йЎ№пјӣеңЁзҗҶз”ұж–№йқўпјҢеүҚиҖ…и®Өе®ҡеҘ№вҖңеҸ‘зҺ°дәҶйқ’и’ҝзҙ вҖқпјҢжұӮжҳҜ科еӯҰеҹәйҮ‘дјҡеҲҷи®Өе®ҡеҘ№еңЁ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дёҖдёӘзҺҜиҠӮдёҠпјҢеҚівҖңйҮҮз”Ёд№ҷйҶҡжҸҗеҸ–йқ’и’ҝжҠ—з–ҹжңүж•ҲйғЁеҲҶвҖқзҡ„е·ҘдҪңдёӯпјҢеҸ–еҫ—ж–°жҲҗе°ұгҖӮеңЁиЎЁиҝ°ж–№йқўпјҢеүҚиҖ…еӨҡж¬Ўејәи°ғвҖңејҖеҲӣжҖ§вҖқгҖҒвҖңйҰ–иҰҒвҖқгҖҒвҖңйўҶеҜјвҖқгҖҒвҖңйҰ–ж¬ЎвҖқзӯүгҖӮеҗҺиҖ…еҲҷиҝҗз”ЁвҖңйӣҶдҪ“вҖқгҖҒвҖңеҲҶдә«вҖқгҖҒвҖңеҗҲдҪңвҖқзӯүжңҜиҜӯгҖӮеҜ№жӢүж–Ҝе…ӢеҹәйҮ‘дјҡжқҘиҜҙпјҢйқ’и’ҝзҙ жҳҜеңЁејӮеӣҪеҒҡеҮәзҡ„科еӯҰеҸ‘зҺ°пјҢдё”дёӯеӣҪйӣҶдҪ“е№іеқҮдё»д№үжҖқжғіеҪұе“ҚдёӢеҮәзҺ°зҡ„з§‘з ”жҲҗжһңйӣҶдҪ“зҪІеҗҚгҖҒйӣҶдҪ“иҺ·еҘ–зӯүзҺ°иұЎдҪҝеҫ—дёӘдәә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и®Өе®ҡеҮәзҺ°йҮҚйҮҚиҝ·йӣҫпјҢеҹәйҮ‘дјҡжҲҗе‘ҳпјҲзұіеӢ’В·и·Ҝжҳ“ж–ҜдёҺд»–зҡ„еҗҢдәӢпјүеңЁвҖңжІЎжңүж–ҮзҢ®пјҢжІЎжңүеҮәзүҲи®°еҪ•вҖқ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дәҺ2007е№ҙзқҖжүӢжҺўз©¶йқ’и’ҝзҙ з ”еҸ‘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з»ҸиҝҮж·ұе…Ҙзҡ„и°ғжҹҘз ”з©¶пјҢжңҖз»Ҳи®Өе®ҡеұ е‘Ұе‘Ұзҡ„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гҖӮд»ҘдёҠз§Қз§Қи¶іи§ҒзҫҺ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еҜ№з§‘еӯҰдјҳе…ҲжқғгҖҒдёӘдәәејҖеҲӣжҖ§иҙЎзҢ®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еҸҠдёҺдёӯеӣҪ科еӯҰжүҝи®ӨеҸҠеҘ–еҠұ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дёҚеҗҢзҡ„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зү№иҙЁгҖӮ
е…ідәҺ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еҘ–пјҢдёӯеӣҪдёӯеҢ»з§‘еӯҰйҷўйҷўй•ҝеј дјҜзӨјйҷўеЈ«жҢҮеҮәпјҢвҖңеҘ№пјҲеұ е‘Ұе‘Ұпјү第дёҖдёӘе°ҶдёӯиҚҜйқ’и’ҝеј•е…ҘеҪ“е№ҙзҡ„523йЎ№зӣ®з»„пјҢ第дёҖдёӘжҸҗеҸ–еҮәжқҘдәҶе…·жңүзҷҫеҲҶд№Ӣзҷҫжҙ»жҖ§зҡ„йқ’и’ҝзҙ пјҲ191еҸ·ж ·е“ҒпјүпјҢ第дёҖдёӘе°Ҷе…¶з”ЁеҲ°дёҙеәҠиҖҢиҜҒе®һе®ғжңүж•ҲвҖқ[11]гҖӮйҘ¶жҜ…гҖҒй»Һж¶ҰзәўгҖҒеј еӨ§еәҶд№ҹи®ӨдёәпјҢвҖңеұ е‘Ұе‘ҰеңЁ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Ҹ‘зҺ°иҝҮзЁӢдёӯиө·дәҶе…ій”®жҖ§зҡ„дҪңз”ЁвҖқпјҢе…¶зҗҶз”ұд№ҹжңүдёүжқЎпјҢвҖңпјҲ1пјүеұ е‘Ұе‘ҰжҸҗеҮәз”Ёд№ҷйҶҡжҸҗеҸ–еҜ№дәҺ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ҡ„жҠ—з–ҹдҪңз”Ёе’ҢиҝӣдёҖжӯҘз ”з©¶йқ’и’ҝйғҪеҫҲе…ій”®гҖӮпјҲ2пјүе…·дҪ“еҲҶзҰ»зәҜеҢ–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й’ҹиЈ•е®№пјҢжҳҜеұ е‘Ұе‘ҰиҜҫйўҳз»„зҡ„жҲҗе‘ҳгҖӮпјҲ3пјүе…¶д»–жҸҗеҸ–еҲ°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°Ҹз»„жҳҜеңЁдјҡи®®дёҠеҫ—зҹҘеұ е‘Ұе‘Ұе°Ҹз»„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І—жҸҗзү©й«ҳж•ҲжҠ—з–ҹдҪңз”Ёд»ҘеҗҺиҝӣиЎҢе·ҘдҪңзҡ„пјҢиҺ·еҫ—зәҜеҢ–еҲҶеӯҗд№ҹжҷҡдәҺй’ҹиЈ•е®№вҖқ[4]гҖӮеҸҜи§ҒпјҢдёӯеӣҪд№ҹжңү科еӯҰ家е’ҢеӯҰиҖ…еӣ вҖң第дёҖжҖ§вҖқгҖҒвҖңе…ій”®жҖ§вҖқгҖҒвҖңдјҳе…ҲжҖ§вҖқзӯүи®Өдёәеұ е‘Ұе‘ҰдёӘдәәиҺ·еҘ–е…·жңүеҗҲзҗҶжҖ§пјҢд№ҹеҚіи®ӨеҸҜзҫҺеӣҪ科еӯҰеҘ–еҠұзҡ„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д»·еҖјеҸ–еҗ‘гҖӮеұ е‘Ұе‘Ұжң¬дәәеңЁиӮҜе®ҡйӣҶдҪ“иҙЎзҢ®зҡ„еҗҢж—¶и®ӨдёәпјҢиғҪиҺ·еҫ—иҜҘеҘ–йЎ№пјҢжҳҜз”ұдәҺиҜҘеҘ–йҮҚи§Ҷз§‘з ”зҡ„зӢ¬еҲӣжҖ§гҖӮеңЁ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з ”еҸ‘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Ҙ№зҡ„4дёӘзӘҒз ҙжҖ§жҲҗжһңжңҖз»Ҳиөўеҫ—дәҶиҜ„委дјҡзҡ„и®ӨеҸҜпјҡпјҲ1пјүйҰ–еҲӣзҡ„дҪҺжё©жҸҗеҸ–жі•пјӣпјҲ2пјүжҳҺзЎ®дәҶ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科еұһе·®ејӮгҖӮйқ’и’ҝзҙ 科еұһеәһжқӮпјҢжңү5дёӘе“Ғз§ҚпјҢеҘ№зҡ„з§‘з ”еӣўйҳҹйҰ–е…ҲеҸ‘зҺ°пјҢе…¶дёӯд»…A.annua L.иҝҷз§Қйқ’и’ҝеҗ«жңүйқ’и’ҝзҙ пјӣпјҲ3пјүжҳҺзЎ®дәҶе…·жңүжҠ—з–ҹдҪңз”Ёзҡ„жңүж•ҲжҲҗеҲҶеӯҳеңЁдәҺйқ’и’ҝзҡ„еҸ¶зүҮдёӯгҖӮиҖҢеңЁжӯӨд№ӢеүҚпјҢдәә们дёҖзӣҙиҜҜд»Ҙдёәжңүж•ҲжҲҗеҲҶеӯҳеңЁдәҺж•ҙж Әйқ’и’ҝпјӣпјҲ4пјүжҳҺзЎ®дәҶйқ’и’ҝеҸ¶дёӯжңүж•ҲжҲҗеҲҶжңҖй«ҳеҖјзҡ„ж—¶жңҹпјҢеҸӘжңүеңЁеӨҸз§Ӣд№ӢдәӨйқ’и’ҝжһқз№ҒеҸ¶иҢӮж—¶пјҢе…¶жҠ—з–ҹжңүж•ҲжҲҗеҲҶжүҚиҫҫеҲ°еі°еҖј[12]гҖӮ
еңЁејәи°ғ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жӢүж–Ҝе…ӢеҹәйҮ‘дјҡд№ҹ并жңӘеҗҰи®Өеұ е‘Ұе‘Ұеӣўйҳҹе…¶д»–жҲҗе‘ҳе’Ңе…¶д»–еҗҲдҪңжҲҗе‘ҳзҡ„科еӯҰиҙЎзҢ®пјҢжҺҲеҘ–иҜҙжҳҺдёӯеӨҡж¬ЎжҸҗеҲ°вҖңеұ еёҰйўҶеҘ№зҡ„еӣўйҳҹвҖқгҖҒвҖңеҘ№зҡ„еӣўйҳҹвҖқзӯүпјҢеңЁеҸҷиҝ°йқ’и’ҝзӯӣйҖүиҝҮзЁӢж—¶пјҢз”ЁвҖңеұ е’ҢеҘ№зҡ„еӣўйҳҹвҖқпјҲжҢҮдҪҷдәҡзәІе’ҢйЎҫеӣҪжҳҺпјүпјӣеңЁи®ІвҖң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ҲҶзҰ»е’ҢзәҜеҢ–вҖқж—¶з”ЁвҖңеҘ№е’ҢеҘ№зҡ„еҗҢдәӢвҖқпјҲжҢҮй’ҹиЈ•е®№пјүпјӣеңЁжҸҗеҲ°йқ’и’ҝзҙ дёҙеәҠиҜ•йӘҢж—¶з”ЁвҖңе…¶д»–з ”з©¶жүҖзҡ„и®ёеӨҡ科еӯҰ家вҖқпјҢзқҖйҮҚд»Ҙд»Ӣз»ҚеҸӮдёҺиҖ…姓еҗҚгҖҒе·ҘдҪңеҚ•дҪҚгҖҒеҸӮдёҺж—¶й—ҙе’Ңе…·дҪ“иҙЎзҢ®зҡ„ж–№ејҸиӮҜе®ҡдәҶвҖң20дё–зәӘ70е№ҙд»ЈдёӯжңҹејҖе§Ӣ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еҸҠе…¶зұ»зү©иҙЁиҝӣиЎҢдёҙеәҠиҜ•йӘҢзҡ„жқҘиҮӘе№ҝе·һдёӯеҢ»иҚҜеӨ§еӯҰзҡ„жқҺеӣҪжЎҘвҖқе’ҢвҖң1980е№ҙеҠ е…ҘжқҺиЎҢеҲ—зҡ„жқҘиҮӘйҰҷжёҜиҝңдёңзҪ—ж°Ҹз ”з©¶еҹәйҮ‘дјҡзҡ„еҹәжҖқВ·йҳҝиҜәеҫ·пјҲKeith ArnoldпјүвҖқ[9]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дёҙеәҠе·ҘдҪңж–№йқўзҡ„еҚ“и¶ҠиҙЎзҢ®гҖӮ
и®Ёи®әеҰӮдҪ•еӨ„зҗҶ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ҹ
еҰӮдёҠж–ҮпјҢдёӯзҫҺ科еӯҰеҘ–еҠұеҜ№йқ’и’ҝзҙ иҺ·еҘ–зҡ„еӨ„зҗҶеӯҳеңЁжҳҺжҳҫе·®ејӮпјҢдёӯеӣҪејәи°ғйӣҶдҪ“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еҖҫеҗ‘дәҺ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е…јйЎҫдёӘдәәпјҢзҫҺеӣҪејәи°ғдёӘдәә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еҖҫеҗ‘дәҺвҖңдёӘдәәеңЁеңәвҖқе…јйЎҫе…¶д»–дёӘдәәпјҢдәҢиҖ…йғҪжІЎжңүеҶіз„¶еҗҰи®ӨдёӘдәәжҲ–йӣҶдҪ“зҡ„иҙЎзҢ®гҖӮ
жңүдәәи®Өдёә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дёҺйқ’и’ҝзҙ еңЁдёӯеӣҪиҺ·еҫ—йӣҶдҪ“еҘ–пјҢеұһеҺҶеҸІйҒ—з•ҷй—®йўҳпјҢеҸ—дёӯеӣҪе»әеӣҪеҲқжңҹйҳ¶ж®өз”ҡиҮід»ҘеҗҺеҫҲй•ҝж—¶й—ҙзҡ„йӣҶдҪ“дё»д№үе’Ңе№іеқҮдё»д№үи§ӮеҝөеҪұе“ҚгҖӮдёҺе…¶д»–йўҶеҹҹзӣёжҜ”пјҢж–°дёӯеӣҪйҖҡиҝҮ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иҫғж—©ең°еңЁз»ҸжөҺйўҶеҹҹеј•е…ҘжіЁйҮҚдёӘдҪ“зҡ„еёӮеңәз«һдәүжңәеҲ¶пјҢзӣҙеҲ°д»ҠеӨ©пјҢеёӮеңәз«һдәүжңәеҲ¶еңЁжҲ‘еӣҪз»ҸжөҺйўҶеҹҹиҝҗиЎҢиүҜеҘҪпјҢдҪҶжҲ‘еӣҪз»ҸжөҺд№ҹд»ҚеӨ„дәҺи®ЎеҲ’еҲ°еёӮеңәзҡ„иҪ¬еһӢжңҹгҖӮе…¶д»–йўҶеҹҹж·ұеҸ—з»ҸжөҺйўҶеҹҹеёӮеңәеҢ–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иҪ¬еһӢеҚҙжӣҙеҠ зј“ж…ўе’Ңж»һеҗҺпјҢеңЁз§‘жҠҖйўҶеҹҹд№ҹеҰӮжҳҜпјҢж”ҝеәңеҜ№з§‘жҠҖзҡ„е®Ҹи§Ӯи®ЎеҲ’е’ҢеҪұе“Қдҫқ然иҫғеӨ§пјҢеңЁз§‘жҠҖеҘ–еҠұйўҶеҹҹзҡ„жҳҫжҖ§иЎЁзҺ°еҚідёҺеҢ…жӢ¬зҫҺеӣҪеңЁеҶ…зҡ„иҘҝж–№еӣҪ家зӣёеҸҚпјҢжҲ‘еӣҪж”ҝеәңеҘ–еӨҡдәҺж°‘й—ҙеҘ–пјҢж”ҝеәңеҘ–зҡ„еЈ°жңӣй«ҳдәҺж°‘й—ҙеҘ–пјҢдё”ж”ҝеәңеҘ–еӨ§еӨҡжҳҜжҲҗжһңеҘ–пјҢж•…еңЁдёӯеӣҪ科жҠҖеҘ–еҠұз»“жһ„дёӯпјҢжҲҗжһңеҘ–еӨҡдәҺдәәзү©еҘ–[13]гҖӮжҲҗжһңеҘ–еӨҡеҲҷд»Қ然ж„Ҹе‘ізқҖеҜ№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зҡ„йҮҚи§ҶгҖӮ
дёӯиҘҝ科еӯҰеҘ–еҠұеҜ№йӣҶдҪ“е’ҢдёӘдәәеҗ„жңүеҖҫеҗ‘пјҢеҺҳ清科еӯҰеҘ–еҠұзҡ„е®һиҙЁе’Ңзӣ®зҡ„жҳҜе…¬е…ҒеӨ„зҗҶ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дёӘдәәдёҺйӣҶдҪ“зҡ„е…ій”®жүҖеңЁгҖӮй»ҳйЎҝи®ӨдёәпјҢвҖң科еӯҰеҲ¶еәҰжҠҠзӢ¬еҲӣжҖ§и§ЈйҮҠдёәдёҖз§ҚжңҖй«ҳзҡ„д»·еҖјпјҢеӣ жӯӨдҪҝеҫ—дёҖдёӘдәәзҡ„зӢ¬еҲӣжҖ§жҳҜеҗҰиғҪеҫ—еҲ°жүҝи®Ө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дәӢе…ійҮҚеӨ§зҡ„й—®йўҳвҖқ[14]гҖӮдҪҶеҜ№зӢ¬еҲӣжҖ§зҡ„иҝҪжұӮжҳҜеҗҰдёҖе®ҡиҰҒдёҺдёӘдәәеҜјеҗ‘зҡ„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иҒ”зі»еңЁдёҖиө·е‘ўпјҹиҝҷж¶үеҸҠеҲ°еҘ–еҠұдёҺдёӘдәәиҙўдә§жқғ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й—®йўҳгҖӮдәӢе®һдёҠпјҢ科еӯҰеҘ–еҠұж„Ҹе‘ізқҖиөӢдәҲ科еӯҰ家пјҲдёҚи®әжҳҜдёӘдәәиҝҳжҳҜйӣҶдҪ“пјүдёҖз§Қиҙўдә§жқғпјҢвҖңеңЁз§‘еӯҰдёӯпјҢиҷҪ然没жңүжҲ‘们йҖҡеёёдҪҝз”Ёж„Ҹд№үдёӢзҡ„иҙўдә§еӯ—ж ·пјҢдҪҶжҳҜпјҢ科еӯҰ家确е®һжӢҘжңүиҙўдә§зҡ„дёҖз§Қд»ЈзҗҶеҪўејҸвҖ”вҖ”жүҝи®ӨгҖӮвҖқ[15]еҪ“ж•ҙдёӘзӨҫдјҡзҡ„дә§жқғеҲ¶еәҰд»Ҙ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дёәеҹәзЎҖпјҢ科еӯҰзҡ„иҝҷз§ҚеҘ–еҠұеҝ…然иҰҒд»ҘзӘҒеҮәдёӘдәәеҘ–еҠұдёәеҹәжң¬еҜјеҗ‘гҖӮ
科еӯҰеҘ–еҠұзҡ„е®һиҙЁеҚіеҜ№з§‘еӯҰеҸ‘зҺ°зӢ¬еҲӣжҖ§е’Ң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жүҝи®Өе’ҢеҘ–еҠұпјҢиҝҷз§Қжүҝи®Өе’ҢеҘ–еҠұзҡ„зӣ®зҡ„жҳҜиҝӣдёҖжӯҘжҝҖеҠұ科еӯҰ家们еҜ№зӢ¬еҲӣжҖ§е’Ң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иҝҪжұӮпјҢдҪҝеҫ—科еӯҰд»Ҙиҫғеҝ«зҡ„йҖҹеәҰеўһй•ҝ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ҰӮжһңд»ҘзӢ¬еҲӣжҖ§дёә科еӯҰзҡ„жңҖй«ҳд»·еҖјпјҢеңЁ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зӨҫдјҡдҪ“зі»дёӯпјҢдёҚз®ЎжҳҜд»ҺзҗҶи®әзҡ„иҝҳжҳҜе®һз”Ёзҡ„и§’еәҰзңӢпјҢ科еӯҰеҘ–еҠұйғҪе°Ҷд»ҘдёӘдәәеҘ–еҠұдёәдё»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йӣҶдҪ“еҗҲдҪңзҡ„з§‘з ”жҙ»еҠЁпјҢд№ҹйңҖиҰҒжҠҠ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зӢ¬еҲӣжҖ§иҙЎзҢ®еҪ’зәҰеҲ°дёӘдҪ“科еӯҰ家иә«дёҠгҖӮ
е°ұжҺҲдәҲеұ е‘Ұе‘ҰзҫҺеӣҪжӢүж–Ҝе…ӢдёҙеәҠеҢ»еӯҰеҘ–иҖҢиЁҖпјҢе°Ҫз®Ў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д»Һиө„йҮ‘гҖҒзү©иҙЁжқЎд»¶гҖҒдәәеҠӣзӯүж–№йқўдёәе…¶жҸҗдҫӣдәҶзҺҜеўғжқЎд»¶пјҢе°Ҫз®ЎдҪҷдәҡзәІзӯүеңЁиҚҜзү©зӯӣйҖүдёӯй”Ғе®ҡдәҶйқ’и’ҝпјҢжқҺеӣҪжЎҘзӯүдёә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дёҙеәҠеә”з”ЁеҒҡеҮәдәҶе·ЁеӨ§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дёӘдәәд»Ҙд№ҷйҶҡжҸҗеҸ–йқ’и’ҝеҚҙжҳҜж•ҙдёӘ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ңҖе…·зӘҒз ҙжҖ§е’ҢеҶіе®ҡжҖ§зҡ„дёҖжӯҘпјҢд»ҘзӢ¬еҲӣжҖ§е’Ң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Җ§дёәж ҮеҮҶпјҢд»ҺжҠҠиҝҷз§ҚзӢ¬еҲӣжҖ§зҡ„еҸ‘зҺ°иҪ¬еҢ–дёә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зҡ„еҲ¶еәҰи®ҫи®ЎеҮәеҸ‘пјҢеұ е‘Ұе‘ҰдёӘдәәиў«жҺҲдәҲ科еӯҰеҘ–ж— з–‘жҳҜжңүеҗҲзҗҶд№ӢеӨ„зҡ„гҖӮ
жҜ”иҫғиҖҢиЁҖпјҢдёҚи®әжҳҜеңЁ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е®һж–Ҫд»ҘеҸҠеҸ‘зҺ°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иҝҳжҳҜеңЁжӯӨеҗҺзӣёеҪ“й•ҝзҡ„ж—¶й—ҙеҶ…пјҢжҲ‘еӣҪзҡ„дә§жқғз»“жһ„жҲ–иҖ…жҖ»дҪ“дёҠжҳҜд»Ҙе…¬е…ұдә§жқғдёәдё»пјҢжҲ–иҖ…еӨ„дәҺд»Һејәи°ғе…¬е…ұдә§жқғеҗ‘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иҪ¬еһӢзҡ„иҝҮзЁӢд№ӢдёӯпјҢеңЁ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йӣҶдҪ“еҚҸдҪңз ”з©¶дёӯзҡ„科еӯҰ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зЎ®и®ӨпјҢд»ҘеҸҠеҜ№иҝҷз§Қ科еӯҰеҸ‘зҺ°дјҳе…Ҳжқғзҡ„еҘ–еҠұйғҪдёҚе®Ңе…ЁжҳҜд»Ҙ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дёәеҹәзЎҖзҡ„гҖӮйӣҶдҪ“дё»д№үзҡ„д»·еҖјеҜјеҗ‘пјҢд»ҘеҸҠдёҚжҳҺжҷ°зҡ„дә§жқғе…ізі»зӣҙжҺҘең°еҪұе“ҚзқҖ科еӯҰеҘ–еҠұиҝҮзЁӢдёӯиҙўдә§жқғзҡ„еҲҶй…ҚгҖӮ
вҖңйӣҶдҪ“еңЁеңәвҖқзҡ„з»“жһңжҳҜдҪҝеҫ—дёӘдҪ“еҜ№з§‘еӯҰеҸ‘зҺ°зҡ„дјҳе…Ҳжқғиў«жЁЎзіҠеҢ–пјҢеңЁиҝҷз§Қд»·еҖји§Ӯеҝөе’ҢеҲ¶еәҰз»“жһ„дёӢеҰӮдҪ•жҝҖеҠұ科еӯҰ家们иҝҪжұӮзӢ¬еҲӣжҖ§пјҢ并еҒҡеҮәйҮҚиҰҒзҡ„科еӯҰеҸ‘зҺ°пјҢе…¶дёӯзҡ„жҝҖеҠұжңәеҲ¶еҰӮдҪ•еҸ‘жҢҘдҪңз”ЁеҖјеҫ—иҝӣдёҖжӯҘжҺўи®ЁгҖӮеңЁд»ҺйӣҶдҪ“дә§жқғеҗ‘дёӘдәәдә§жқғиҝҮжёЎзҡ„зӨҫдјҡиҪ¬еһӢиҝҮзЁӢдёӯпјҢ科еӯҰжүҝи®Өдёӯзҡ„йӣҶдҪ“еҲҶдә«д№ҹеҫҲе®№жҳ“еј•еҸ‘дә§жқғзә зә·пјҢдҫӢеҰӮйқ’и’ҝзҙ иҝӣе…Ҙз”ҹдә§еҗҺпјҢз”ұдәҺиҝҮж—©е…¬ејҖ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е’ҢдёӯеӣҪеҜ№з§‘еӯҰ家зҡ„йӣҶдҪ“еЎ‘йҖ иҖҢеј•еҸ‘дәҶдёҖзі»еҲ—дә§жқғзә зә·зӯүгҖӮ
жҖ»дҪ“дёҠзңӢпјҢд»ҘжҝҖеҠұ科еӯҰ家дёӘдҪ“дёәзү№еҫҒзҡ„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еҜ№дҝғиҝӣ科еӯҰ家еҒҡеҮәзӢ¬еҲӣжҖ§зҡ„еҸ‘зҺ°ж— з–‘жҳҜжңүж•Ҳзҡ„гҖӮдҪҶиҝҷз§ҚеҲ¶еәҰиҝңйқһе®ҢзҫҺпјҢй»ҳйЎҝзӯүдәәеҸ‘зҺ°зҡ„вҖң马еӨӘж•Ҳеә”вҖқзӯүзҺ°иұЎе°ұиҜҙжҳҺдәҶиҝҷз§ҚеҲ¶еәҰеӯҳеңЁзҡ„зјәйҷ·гҖӮеҰӮдҪ•еңЁеҲ¶еәҰи®ҫи®ЎдёӯжӣҙеҘҪең°еӨ„зҗҶ科еӯҰеҘ–еҠұдёӯйӣҶдҪ“дёҺдёӘдҪ“зҡ„е…ізі»д»Қ然жҳҜдёҖдёӘеҖјеҫ—з ”з©¶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
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
[1]иғЎе…¶еі°. йҷҲе»әејә. йҹ©еҗҜеҫ·пјҡеҘ–йЎ№иҝҮеӨҡеҠ©й•ҝеӯҰжңҜжө®иәҒ[N].е…үжҳҺж—ҘжҠҘпјҢ2011-9-22.
[2]еј еү‘ж–№. иҝҹеҲ°зҡ„жҠҘе‘ҠвҖ”вҖ”дә”дәҢдёүйЎ№зӣ®дёҺйқ’и’ҝзҙ з ”еҸ‘зәӘе®һ[M]. е№ҝе·һпјҡзҫҠеҹҺжҷҡжҠҘеҮәзүҲзӨҫпјҢ2006:85,123.
[3]еӣҪ家科еӯҰжҠҖжңҜ委е‘ҳдјҡ. жҖ»еҗҺеӢӨйғЁ. з–ҹз–ҫйҳІжІ»иҚҜзү©з ”究е·ҘдҪңеҚҸдҪңдјҡи®®зәӘиҰҒ[R]пјҢ1967-6-16.
[4] ]йҘ¶жҜ…. й»Һж¶Ұзәў. еј еӨ§еәҶ. дёӯиҚҜзҡ„科еӯҰз ”з©¶дё°зў‘[J] . 科еӯҰж–ҮеҢ–иҜ„и®әпјҢ2011пјҲ4пјү:33,37,38,41,27-41.
[5]й»Һж¶Ұзәў.вҖң523д»»еҠЎвҖқдёҺйқ’и’ҝжҠ—з–ҹдҪңз”Ёзҡ„еҶҚеҸ‘зҺ°[J].дёӯеӣҪ科жҠҖеҸІжқӮеҝ—пјҢ2011пјҲ4пјү:497,488-500.
[6]еҲҳеӨ©дјҹ. еұ е‘Ұе‘Ұйҡҗзһ’дёҚжҠҘйқ’и’ҝзҙ еҸ‘жҳҺиҝҮзЁӢдёӯд»–дәәзҡ„еҺҹе§ӢеҸ‘жҳҺ. 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u/twsliu.2011е№ҙ1жңҲ6ж—Ҙи®ҝй—®.
[7]йҘ¶жҜ…. йқ’и’ҝдҪңз”ЁеҸ‘зҺ°зҡ„е…ҲеҗҺпјҡдҪҷдәҡзәІгҖҒйЎҫеӣҪжҳҺе’Ңеұ е‘Ұе‘Ұ. 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blog-2237-514557.html. 2012е№ҙ12жңҲ26ж—Ҙи®ҝй—®.
[8]еј ж–ҮиҷҺ. еҲӣж–°дёӯзҡ„зӨҫдјҡе…ізі»пјҡеӣҙз»•йқ’и’ҝзҙ зҡ„еҮ дёӘдәүи®ә[J]. иҮӘ然иҫ©иҜҒжі•йҖҡи®ҜпјҢ2009пјҲ6пјү:36,32-39.
[9]EvelynStrauss. Lasker.~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. Award Description.Tu-Youyou. http://www.laskerfoundation.org/awards/2011_c_description.htmпјҢ2012е№ҙ12жңҲ27ж—Ҙи®ҝй—®.
[10]е®ӣиҸҠ. еұ е‘Ұе‘ҰиҺ·жӢүж–Ҝе…ӢеҘ–жҝҖиө·зҡ„вҖҰвҖҰ[J]. еҲӣ新科жҠҖ.2011пјҲ6пјү:36,34-37.
[11]й«ҳж–°еҶӣ. еұ е‘Ұе‘ҰпјҡиҝҷжҳҜдёӯеҢ»иө°еҗ‘дё–з•Ңзҡ„иҚЈиӘү[N]. дёӯеӣҪдёӯеҢ»иҚҜжҠҘпјҢ2011-11-16.
[12]еҙ”иҠі. жҲ‘еёҢжңӣеёҰеӣһдёҖдёӘж–°зҡ„жҝҖеҠұжңәеҲ¶пјҡеұ е‘Ұе‘Ұж„ҹиЁҖиҺ·жӢүж–Ҝе…ӢеҘ–еңЁдәҺйқ’и’ҝзҙ з ”з©¶дёӯзҡ„еӣӣдёӘзӘҒз ҙ[N]. еҒҘеә·жҠҘпјҢ2011-11-16.
[13]жҲҗиүҜж–Ң. жқҺжҷ“з«Ӣ. зҺӢзӮҺеқӨ. дёӯеӨ–科жҠҖеҘ–еҠұеҲ¶еәҰзҡ„дё»иҰҒеҢәеҲ«[J]. 科еӯҰжҠҖжңҜдёҺиҫ©иҜҒжі•.1998пјҲ5пјү:41-43.
[14][зҫҺ]R.K.й»ҳйЎҝ. 科еӯҰзӨҫдјҡеӯҰпјҲдёӢпјү[M]. еҢ—дә¬пјҡе•ҶеҠЎеҚ°д№ҰйҰҶпјҢ2003:125.
[15]Cole, J. R. and Cole, J. S.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[M], Chicago: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1973: 45.
|
| |
| | |




.jpg)







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