е…ідәҺеӣҪзІ№дә¬еү§зҡ„еҲ«жҖқ | 2013-05-30 14:05:20 (иў«йҳ…иҜ» 859 ж¬Ў) |  | дә¬еү§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иөўеҫ—жӣҙеӨҡзҡ„и§Ӯдј—пјҢиҺ·еҫ—зңҹиҜҡзғӯзҲұе®ғзҡ„вҖңдәәеҝғвҖқгҖӮеҗҰеҲҷпјҢеҰӮжһңеҸӘеҒҸйҮҚдәҺжһҒе°‘ж•°вҖңй—ЁеҶ…дәәвҖқиҮӘжҲ‘ж¬ЈиөҸпјҢжҲ–е°‘ж•°еӯҰе”ұдә¬еү§зҡ„й…·зҲұиҖ…зӣёдә’йҷ¶йҶүпјҢз»ҲжҳҜйҡҫд»Ҙж”№еҸҳдә¬еү§дёҺе№ҝеӨ§е…¬дј—зӣёз–ҸзҰ»зҡ„зәҜвҖңеҶ…иЎҢеҢ–вҖқзҡ„еұҖйқўгҖӮ
гҖҖгҖҖжҲ‘жүҖжҺҘи§Ұ并еҒҡиҝҮи®ӨзңҹдәҶи§Јзҡ„иҝҷдәӣжҜ”иҫғе№ҙиҪ»зҡ„и§Ӯдј—пјҢеӨ§йғҪжӢҘжңүиҫғдё°еҜҢзҡ„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пјҢд№ҹжҺҢжҸЎеҝ…еӨҮзҡ„еҺҶеҸІи§ӮзӮ№пјҢ他们зҗҶи§Јдј з»ҹдә¬еү§дә§з”ҹ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пјҢ并дёҚе®Ңе…Ёд»Ҙд»Ҡдәәзңје…үеҺ»иЎЎйҮҸпјҢжӣҙдёҚиӢӣжұӮдә¬еү§жҜҸдёӘеү§зӣ®жүҖеҸҚжҳ еҮәзҡ„жҖқжғійғҪиҰҒеҗҲдәҺд»ҠдәәвҖңе°әеҜёвҖқгҖӮй—®йўҳжҳҜдёҚиғҪзҰ»еӨ§и°ұпјҢд№ҹдёҚеҸҜеҜ№жҳҺжҳҫйҷҲи…җзҡ„дёңиҘҝжҙҘжҙҘд№җйҒ“гҖӮиҝҷдәӣжүҚжҳҜ他们жңүжүҖвҖңжҢ‘еү”вҖқзҡ„гҖӮ
е…ідәҺеӣҪзІ№дә¬еү§зҡ„еҲ«жҖқвҖ”вҖ”е…јдёҺе№ҙиҪ»жңӢеҸӢдёҖиө·зңӢжҲҸжүҖж„ҹ
гҖҖгҖҖжүҖи°“дә¬еү§зҡ„йҒ“еҫ·еҶ…ж¶ө既然жҳҜ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жүҖеҪўжҲҗпјҢеҝ…е®ҡдҝқжңү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дјҰзҗҶеҶ…ж ёгҖӮеҚідҪҝдёҺд»ҠеӨ©жҲ‘们жүҖйңҖиҰҒзҡ„йҒ“еҫ·еҸ–еҗ‘йҮҚеҗҲпјҢд№ҹеҸӘиғҪиҜҙе®ғеңЁдёҚеҗҢж—¶д»ЈжңүзӣёиҝһжҺҘзӣёз»§жүҝзҡ„дёҖйқў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®Ңе…ЁжІЎжңүеҝ…иҰҒжңҹжңӣдә¬еү§жӢ…еҪ“йҒ“еҫ·ж•ҷеҢ–иҖ…зҡ„йҮҚиҙҹгҖӮеӣ дёәдә¬еү§жҳҜдёҖй—ЁеҸӨиҖҒзҡ„иүәжңҜпјҢдә¬еү§е°ұжҳҜдә¬еү§гҖӮ
笔иҖ…жҳҜдёҖдёӘдә¬еү§зҡ„зҲұеҘҪиҖ…пјҢиҮӘе№јеңЁиғ¶дёңиҖҒ家е°ұйҡҸеӨ§дәәзңӢдәҶдёҚе°‘вҖңиҖҒжҲҸвҖқпјҢе°‘е№ҙж—¶д»ЈеҸӮеҶӣеҗҺд№ҹзңӢдәҶдёҚе°‘йғЁйҳҹдә¬еү§еӣўзҡ„жј”еҮәпјҢиҝӣеҹҺеҗҺе…¬дј‘ж—Ҙзҡ„еӨ§йғЁеҲҶж—¶й—ҙд№ҹиҠұеңЁиҮӘе·ұд№°зҘЁзңӢжҲҸдёҠдәҶпјҢзӣҙиҮівҖңж–Үйқ©вҖқжүҚе‘Ҡдёӯж–ӯгҖӮзІүзІ№вҖңеӣӣдәәеё®вҖқеҗҺдј з»ҹдә¬еү§еҶҚзҺ°иҲһеҸ°пјҢжҲ‘еҸҲйҮҚжё©иҝҷз§Қдёӯж–ӯдәҶж•°е№ҙзҡ„еӣәжңүзҡ„ејәзғҲзҲұеҘҪгҖӮиҷҪ然еӣ дёәе·ҘдҪңеҝҷзңӢжҲҸдёҚдјјеҪ“е№ҙеҜҶеәҰйӮЈд№ҲеӨ§пјҢдҪҶжңүе…іж–№йқўеҜ№дә¬еү§дҪңдёәеӣҪзІ№зҡ„йҮҚи§ҶдёҺеҗ„ж–№йқўзҡ„жҺЁеҠ©пјҢиҝҳжҳҜдҪҝжҲ‘еҸ—еҲ°дәҶеҫҲеӨ§зҡ„йј“иҲһпјҢд№ҹе§Ӣз»ҲдёҚжёқең°е…іжіЁдә¬еү§зҡ„еҸ‘еұ•гҖӮ
гҖҖгҖҖ然иҖҢпјҢиҜҙе®һиҜқпјҢд»Һж„ҹжғ…дёҠзғӯзҲұз”ҡиҮіеҒҸеҘҪдә¬еү§еӣә然жҳҜеҹәжң¬зҡ„пјҢдҪҶеҜ№е®ғеңЁеқҡе®Ҳе’ҢеҸ‘еұ•е®һи·өдёӯзҡ„жҹҗдәӣж–№йқўе§Ӣз»ҲжңүдёҖдәӣжғіжі•пјҢд»ҘзҗҶжҖ§и§Ӯз…§дә¬еү§пјҢдёҚиғҪдёҚеј•еҸ‘дәҶдёҖдәӣжҖқиҖғгҖӮж—©е°ұжғіжӢ©иҰҒжҸҗеҮәжң¬дәәзҡ„зңӢжі•е’Ңж„Ҹи§ҒпјҢдҪҶеӣ иҖғиҷ‘еҲ°е®ғжҜ•з«ҹжҳҜдә§з”ҹдәҺ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дёҖдёӘеҸӨиҖҒеү§з§ҚпјҢе°Ҫз®ЎеӯҳеңЁзқҖиҝҷж ·жҲ–йӮЈж ·зҡ„вҖңдёҚйҖӮвҖқд№ғиҮід»ҠеӨ©д»Өдәәзә з»“д№ӢеӨ„пјҢиҝҳжҳҜи§үеҫ—еә”з»ҷдәҲе°ҪеӨҡзҡ„е®Ҫе®№гҖӮиҖҢеҶөпјҢдј—еӨҡеҘҪеҝғзҡ„жҠӨжҢҒиҖ…еҜ№дә¬еү§зҙ жқҘжҠұжңүеӨӘеӨҡзҡ„зҸҚзҲұдёҺжңҹеҫ…пјҢеҫҲе°‘жңүеҜ№е…¶иҙҹйқўзҡ„еЈ°йҹіиЎЁиҫҫпјҢеӣ иҖҢеңЁжҲ‘еҶ…еҝғд№ҹе°ұвҖңжЁЎзіҠеӨ„зҗҶвҖқ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дҪҶеҲ°еҗҺжқҘпјҢеҗ¬жңү关专家讲иҝ°пјҢеҗ¬дә¬еү§з”өи§ҶеӨ§еҘ–иөӣжҹҗдәӣиҜ„委е’Ңдё»жҢҒдәәеёёеёёеҖҫеҗ‘дәҺиҜҙдә¬еү§еҜ№дәҺдј ж’ӯ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е°Өе…¶жҳҜиҝӣиЎҢдј з»ҹйҒ“еҫ·ж•ҷиӮІжҳҜеӨҡд№ҲеӨҡд№Ҳзҡ„йҮҚиҰҒпјҢдҝғдҪҝжҲ‘дёҚиғҪдёҚиҜҙеҮәжҲ‘дёҖзӣҙжғіиҜҙзҡ„иҜқпјҢд№ҹи®ёжӯЈеӣ дёәеҮәдәҺеҜ№еӣҪзІ№зҡ„иЎ·еҝғзҲұжҠӨ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дёәжӣҙеҘҪең°д»ҺжӯЈйқўе®Јдј е…¶зңҹжӯЈеҖјеҫ—ејҳжү¬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жүҚеә”дҪҝдәә们е°Өе…¶жҳҜе№ҙиҪ»дёҖд»ЈжӯЈзЎ®и®ӨиҜҶдә¬еү§дҪңдёәеӣҪзІ№зҡ„д»·еҖјжүҖеңЁгҖӮиҖҢдёҚжҳҜз”ұдәҺвҖңдҝқжҠӨвҖқе’Ңе®Јдј дёҚеҪ“еҸҚиҖҢеҮҸејұз”ҡиҮідҪҝ他们дә§з”ҹдәҶдёҚеҝ…иҰҒзҡ„иҙЁз–‘гҖӮ
гҖҖгҖҖвҖңд»ҺеЁғеЁғжҠ“иө·вҖқзҡ„иҖҒиҜҫйўҳ
гҖҖгҖҖиҝҷйҮҢдҫҝиҮӘ然зүөж¶үеҲ°дёҖдёӘвҖңд»ҺеЁғеЁғжҠ“иө·вҖқзҡ„иҖҒиҜҫйўҳгҖӮиҝҷдёҖжҸҗжі•ж— з–‘жҳҜеҜ№зҡ„пјҢдҪҶжҲ‘и§үеҫ—иҝ‘е№ҙжқҘеңЁвҖңеЁғеЁғзҘЁеҸӢвҖқзҡ„еҸ‘еұ•жҳҜжҳҫи‘—зҡ„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иҮӘе№јеӯҰе”ұеӯҰжј”дә¬еү§зҡ„е„ҝз«Ҙе°‘е№ҙе°–еӯҗзҡ„зЎ®еҮәдәҶдёҚе°‘пјҢжҳҜиҮӘиЎҢж¶ҢзҺ°иҝҳжҳҜеҗ„ең°жіЁж„ҸвҖңжҠ“вҖқеҮәжқҘзҡ„пјҢжң¬дәәжңӘиҜҰдҪңиҖғеҜҹгҖӮдҪҶжҲ‘зҗҶи§Јзҡ„вҖңд»ҺеЁғеЁғжҠ“иө·вҖқпјҢдёҚеҚ•еҚ•жҳҜеӯҰе”ұдә¬еү§зҡ„дёҖйқўпјҢиҝҳеә”гҖҒз”ҡиҮіжҳҜжӣҙеә”еҢ…жӢ¬дә¬еү§зҡ„еҸ—дј—иҖ…гҖӮеҪ“然пјҢиҝҷдәӣе№ҙпјҢвҖңдә¬еү§иҝӣеӨ§еӯҰвҖқд№ғиҮіиҝӣдёӯе°ҸеӯҰдәҰжҳҜжңүиЎҢеҠЁзҡ„пјҢдҪҶдёҚиғҪдёҚжүҝи®ӨпјҢи·қзҰ»и®ёи®ёеӨҡеӨҡдәәпјҲзү№еҲ«жҳҜе№ҙиҪ»дәәпјүзҲұзңӢзҲұеҗ¬дә¬жҲҸиҝҷдёҖжҜ”иҫғзҗҶжғізҡ„жңҹжңӣеҖјпјҢиҝҳжҳҜжңүдёҖеӨ§ж®өи·ҜиҰҒиө°зҡ„гҖӮе®һдәӢжұӮжҳҜең°иҜҙпјҢжҲ‘们еҝ…йЎ»иҖғиҷ‘еҲ°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еӣ зҙ жҳҜпјҡжҜ•з«ҹжҲ‘们д»ҠеӨ©зҡ„ж—¶д»Је·ІдёҚеҗҢдәҺеҪ“е№ҙдә¬еү§йқһеёёе…ҙзӣӣжңҹзҡ„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ҺҜеўғпјҢеӣ жӯӨиҝҮеҲҶеҘўжңӣд№ҹжҳҜдёҚе®һйҷ…зҡ„гҖӮ
гҖҖгҖҖйҷӨжӯӨиҖҢеӨ–пјҢеә”иҜҘеҠӘеҠӣеҒҡеҲ°зҡ„иҝҳжңүе“Әдәӣе‘ўпјҹе®Јдј еҠӣеәҰзҡ„еҠ ејә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җ„з§Қеҗ„ж ·зҡ„жј”еҮәжүӢж®өзҡ„е……еҲҶеұ•зӨәпјҢи®©жӣҙеӨҡзҡ„дәәи®ӨиҜҶеҲ°еӣҪзІ№зҡ„д»·еҖјпјҢдҪ“е‘іеҲ°дә¬еү§зҡ„зӢ¬зү№йӯ…еҠӣпјӣжӣҙеҘҪең°дёҫеҠһдёҚеҗҢз§Қзұ»зҡ„дә¬еү§еӨ§еҘ–иөӣзҡ„жҙ»еҠЁпјҢдҪҝеҺҹе…ҲжІЎжңүжҺҘи§ҰжҲ–дәҶи§ЈдёҚеӨҡзҡ„еҗ„дёӘйҳ¶еұӮгҖҒеҗ„дёӘе№ҙйҫ„ж®өзҡ„и§Ӯдј—жңүжӣҙеӨҡзҡ„жңәдјҡйүҙиөҸпјҢиҝӣиҖҢжұІеҸ–еҲ°е®ғзҡ„зңҹй«“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иөўеҫ—жӣҙеӨҡзҡ„и§Ӯдј—пјҢиҺ·еҫ—зңҹиҜҡзғӯзҲұе®ғзҡ„вҖңдәәеҝғвҖқгҖӮеҗҰеҲҷпјҢеҰӮжһңеҸӘеҒҸйҮҚдәҺжһҒе°‘ж•°вҖңй—ЁеҶ…дәәвҖқиҮӘжҲ‘ж¬ЈиөҸпјҢжҲ–е°‘ж•°еӯҰе”ұдә¬еү§зҡ„й…·зҲұиҖ…зӣёдә’йҷ¶йҶүпјҢз»ҲжҳҜйҡҫд»Ҙж”№еҸҳдә¬еү§дёҺе№ҝеӨ§е…¬дј—зӣёз–ҸзҰ»зҡ„зәҜвҖңеҶ…иЎҢеҢ–вҖқзҡ„еұҖйқўгҖӮ
гҖҖгҖҖи°Ғд№ҹдёҚиғҪжңҹжңӣжүҖжңүзҡ„и§Ӯдј—йғҪжҲҗдёәдә¬еү§зҡ„иЎҢ家пјҢеҚҙеҸҜд»Ҙеҗёеј•зӣёеҪ“еӨҡзҡ„дәәиғҪеӨҹжҺҘеҸ—д»ҘиҮіе–ңж¬ўе®ғгҖӮжҚ®жҲ‘жҺҘи§Ұзҡ„дёҖдәӣжңүзӣёеҪ“ж–ҮеҢ–зҙ е…»зҡ„е№ҙиҪ»жңӢеҸӢпјҢ他们дёӯзҡ„еӨ§йғЁеҲҶдәәеҜ№дәҺдҪңдёәеӣҪзІ№зҡ„дә¬еү§жҠұжңүдёҖз§Қе–„ж„Ҹзҡ„жҠӨжҢҒжҖҒеәҰпјҢжңүзҡ„еҲҷеёҰжңүдёҖз§ҚеҘҪеҘҮзҡ„жҺўжұӮеҝғзҗҶпјҢеёҢжңӣжҺҘиҝ‘дә¬еү§е№¶ж·ұеҲҮең°дәҶи§Је®ғгҖӮеңЁжңүдәҶиҫғеӨҡзҡ„жҺҘи§Ұд№ӢеҗҺпјҢ他们дёӯдёҖеҚҠд»ҘдёҠзҡ„дәәзңҹзҡ„дә§з”ҹдәҶдәІиҝ‘ж„ҹпјҢжңүдәҶеҲқжӯҘзҡ„е…ҙи¶ЈгҖӮиҮіе°‘жҳҜеҜ№дә¬еү§дјҳзҫҺзҡ„е”ұи…”еўһеҠ дәҶеҘҪж„ҹпјҢжёҗж¬ЎеҸҲдёәжҹҗдәӣиЎҢеҪ“е’Ңи§’иүІзҡ„жңҚиЈ…жүҖејәзғҲеҗёеј•пјӣеҶҚеҸҲеҜ№дёҖдәӣи§’иүІиҷҡжӢҹиҖҢз»Ҷи…»зҡ„еҒҡе·ҘжңүдәҶиҫғеҘҪзҡ„дәҶи§Јпјӣжңүзҡ„д№ҹе–ңж¬ўзҒ«зҲҶзҡ„жӯҰжү“еҠҹеӨ«е’ҢзғӯзғҲзҡ„еңәйқўвҖҰвҖҰз»ҸжҲ‘иҝӣдёҖжӯҘдәҶи§ЈпјҢ他们еҜ№еҘҪеҗ¬зҡ„е”ұж®өжңҖдёәиөһиөҸпјҢеҜ№зІҫеҪ©зҡ„жҠҳеӯҗжҲҸзҡ„е…ҙи¶ЈиҝңиғңиҝҮе…ЁеҮәеӨ§жҲҸпјҢеҜ№еңәйқўе’ҢиЎЁжј”дёҠзҡ„иҷҡжӢҹжүӢжі•з”ұдёҚд№ жғҜиҖҢйҖҗжёҗд№ жғҜпјҢеҜ№и„ёи°ұзҡ„з§Қз§Қ讲究з”ұдёҚзҗҶи§ЈиҖҢжңүдәҶеҲқжӯҘзҡ„йўҶз•ҘпјҢеҜ№д№җйҳҹвҖңж–ҮжӯҰеңәвҖқзҡ„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д№ҹжңүдәҶжӣҙеӨҡзҡ„е…іжіЁ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他们дёӯзҡ„дёҚе°‘дәәеҜ№жҹҗдәӣзЁӢејҸеҢ–иҝҮзЁӢпјҲеҰӮвҖңиө·йңёвҖқзӯүпјүиЎЁзӨәдёҚеӨҹзҗҶи§Јд№ғиҮідёҚеӨҹиҖҗзғҰпјӣеҜ№жҹҗдёӘиЎҢеҪ“еҰӮе°Ҹз”ҹзҡ„е”ұжі•е’Ң笑声зӯүиҝҳжңүж¬ д№ жғҜпјӣеҜ№дәҺжӯҰжү“дёӯзҡ„вҖңд№ұжү“вҖқпјҲеҚідҫ§йҮҚзӮҪзғҲж•ҲжһңиҖҢеҝҪз•Ҙйҳөзәҝзҡ„еҲҶжҳҺпјүд»ҘеҸҠжӯҰж—Ұжңүж—¶иҝҮдәҺиҝҪжұӮвҖңжү“еҮәжүӢвҖқзҡ„зҒ«зғҲд№ҹжңүжүҖжҢ‘еү”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иҝҷдәӣжңүзҡ„еҸҜиғҪеұһдәҺжҺҘи§Ұж—¶й—ҙдёҚй•ҝе°ҡйЎ»йҖҗжёҗд№ жғҜпјҢжңүзҡ„д№ҹи®ёеңЁзЁӢејҸе’ҢиЎЁжј”дёҠзЎ®е®һеӯҳеңЁеҖјеҫ—е•ҶжҰ·д№ӢеӨ„пјҢдҪҶе°ҡдёҚз®—жҳҜеӨ§зҡ„йҡңзўҚе’ҢеҺҹеҲҷж–№йқўпјҢдёҚи¶ід»Ҙжһ„жҲҗиҝҷдәӣеұӮйқўзҡ„и§Ӯдј—дёҺдә¬еү§жңүжүҖз–ҸзҰ»жҲ–йҖ жҲҗиҙҹйқўж„ҹгҖӮ
гҖҖгҖҖе№ҙиҪ»и§Ӯдј—зҡ„е®Ҫе®№дёҺвҖңжҢ‘еү”вҖқ
гҖҖгҖҖиҖҢеҪұе“Қиҝҷдәӣе№ҙиҪ»зҡ„жңүиҜҶиҖ…ж„үеҝ«жҺҘеҸ—зҡ„йҮҚиҰҒеӣ зҙ пјҢжҒ°жҒ°еұһдәҺжҲ‘们жҹҗдәӣеҶ…иЎҢ专家з»ҸеёёжҸҗеҸҠзҡ„дёҖдәӣж–№йқўпјҢеҚідә¬еү§зҡ„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д»·еҖје’ҢйҒ“еҫ·ж•ҷеҢ–дҪңз”ЁгҖӮйңҖиҰҒиҜҙжҳҺзҡ„жҳҜпјҢ他们дёҚжҳҜе®Ңе…ЁеҗҰе®ҡиҝҷдәӣж–№йқўзҡ„д»·еҖје’Ңж„Ҹд№үгҖӮеӣ дёәпјҢеҰӮдёҠжүҖиҝ°пјҢжҲ‘жүҖжҺҘи§Ұ并еҒҡиҝҮи®ӨзңҹдәҶи§Јзҡ„иҝҷдәӣжҜ”иҫғе№ҙиҪ»зҡ„и§Ӯдј—пјҢеӨ§йғҪжӢҘжңүиҫғдё°еҜҢзҡ„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пјҢд№ҹжҺҢжҸЎеҝ…еӨҮзҡ„еҺҶеҸІи§ӮзӮ№пјҢ他们зҗҶи§Јдј з»ҹдә¬еү§дә§з”ҹ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пјҢ并дёҚе®Ңе…Ёд»Ҙд»Ҡдәәзңје…үеҺ»иЎЎйҮҸпјҢжӣҙдёҚиӢӣжұӮдә¬еү§жҜҸдёӘеү§зӣ®жүҖеҸҚжҳ еҮәзҡ„жҖқжғійғҪиҰҒеҗҲдәҺд»ҠдәәвҖңе°әеҜёвҖқгҖӮй—®йўҳжҳҜдёҚиғҪзҰ»еӨ§и°ұпјҢд№ҹдёҚеҸҜеҜ№жҳҺжҳҫйҷҲи…җзҡ„дёңиҘҝжҙҘжҙҘд№җйҒ“гҖӮиҝҷдәӣжүҚжҳҜ他们жңүжүҖвҖңжҢ‘еү”вҖқзҡ„гҖӮд»ҘдёӢжҲ‘жғіжҸҗдҫӣ他们зҡ„дёҖдәӣзңӢжі•пјҢжҲ‘и§үеҫ—жҳҜзӣёеҪ“жңүд»ЈиЎЁжҖ§зҡ„гҖӮ
гҖҖгҖҖиҜҙеҲ°д»–们зҡ„зҗҶи§ЈдёҺвҖңе®Ҫе®№вҖқпјҢеҸҜд»ҘдёӨдёӘеү§зӣ®дёәдҫӢпјҡдёҖжҳҜгҖҠй”ҒйәҹеӣҠгҖӢпјҢйҷӨдәҶдҪңе“Ғжң¬иә«зҡ„зІҫж№ӣпјҢдёҚи®әжҳҜзј–жҺ’гҖҒз»“жһ„е°Өе…¶жҳҜе”ұиҜҚж–Үеӯ—зҡ„讲究д»Ө他们иөһиөҸиҖҢеӨ–пјҢеҚідҪҝеҜ№еӣ жһңиҝҳжҠҘзҡ„жһ„жҖқд№ҹз»ҷдәҲе……еҲҶзҗҶи§ЈгҖӮ他们и®ӨдёәиҝҷжҖ»жҳҜдёҖз§Қе–„иЎҢ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з»ҷдәәзҡ„жҖ»дҪ“ж„ҹи§үиҝҳжҳҜиүҜжҖ§зҡ„гҖӮеҸҰдёҖдёӘжҳҜгҖҠзҺүе ӮжҳҘгҖӢпјҢйҷӨдәҶж–Үжң¬е’Ңжј”еҮәдёҠзҡ„еҸҜеҸ–д№ӢеӨ„еӨ–пјҢеҚідҪҝе…Ёеү§зҡ„жҖқжғід№ҹвҖңеҫҲжңүж„ҸжҖқвҖқгҖӮ他们并дёҚиҝҮдәҺи®ЎиҫғдҪңдёәвҖңжҳҺд»ЈвҖқзҡ„зҺӢйҮ‘йҫҷе«–йҷўиҖҢжҢҘйҮ‘еҰӮеңҹпјҢиҝҳжҳҜжӣҙзңӢйҮҚеңЁд»–е’ҢиӢҸдёүд№Ӣй—ҙзҡ„жғ…д№үпјҢи®ӨдёәиҝҷеңЁ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жҳҜжһҒдёәйҡҫеҫ—зҡ„гҖӮиҝҷе°ұе……еҲҶиҜҙжҳҺпјҢжңүзӣёеҪ“ж–ҮеҢ–зҹҘиҜҶеә•и•ҙзҡ„еҪ“д»Је№ҙиҪ»и§Ӯдј—пјҢдёҚд»…иғҪеӨҹзңӢжҮӮдә¬еү§пјҢиҖҢдё”д№ҹжңүеҲҶжһҗзҡ„зңје…үгҖҒиҫ©иҜҒзҡ„жҖҒеәҰгҖӮиҮідәҺжӣҙеӨ§йҮҸзҡ„дә¬еү§еү§зӣ®дёӯжӯЈд№үдёҺйӮӘжҒ¶гҖҒжҡҙиҷҗдёҺе–„иүҜзҡ„йІңжҳҺеҜ№з…§пјҢж°‘ж—ҸжӯЈж°”дёҺеҜ№дҫөз•ҘиҖ…зҡ„дёҚе…ұжҲҙеӨ©пјҢд»ҘеҸҠиӢұйӣ„д№үеЈ«зҡ„жү¶жӯЈжҠ‘йӮӘгҖҒи§Ғд№үеӢҮдёәпјҢжҷ®йҖҡж°‘дј—д№Ӣй—ҙзҡ„зӣёдә’жү¶еҠ©пјҢеј жү¬е…¬жӯЈе№ізӯүзҡ„зҫҺеҘҪдәәжҖ§зӯүзӯүпјҢ他们и®ӨдёәиҝҷдәӣйғҪжҳҜдә¬еү§жӯЈйқўзҡ„гҖҒз„•еҸ‘е…үеҪ©зҡ„йҮҚиҰҒйғЁеҲҶпјҢж— з–‘еұһдәҺдәәж°‘жҖ§зҡ„зІҫеҚҺгҖӮ
гҖҖгҖҖдҪҶ他们并дёҚи®іиЁҖдәӢзү©зҡ„еҸҰдёҖйқўвҖ”вҖ”他们и®Өдёәдә¬еү§дёӯд№ҹеёҰжңүдёҚеҗҢзЁӢеәҰзҡ„йҳҙеҪұйғЁеҲҶгҖӮеңЁд»–们еҜ№жҲ‘иЎЁиҝ°иҝҷзұ»зңӢжі•ж—¶пјҢжҲ‘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№ҙйҫ„дёҠзҡ„й•ҝиҖ…е‘ҠиҜү他们дёҠдё–зәӘдә”еҚҒе№ҙд»Ј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и§Јж”ҫеҲқжңҹпјҢжңүе…ійғЁй—ЁжӣҫеҜ№дә¬еү§еү§зӣ®иҝӣиЎҢиҝҮдёҖз•Әжё…зҗҶпјҢй’ҲеҜ№еҪ“ж—¶и®ӨдёәжҳҜжҳҺжҳҫзҡ„зіҹзІ•йғЁеҲҶпјҲеҰӮжҖқжғіеҶ…е®№жңүеҖҫеҗ‘й—®йўҳпјҢдё‘жҒ¶гҖҒж·«з§ҪзӯүиҲһеҸ°зҺ°иұЎзӯүпјүзҰҒжј”дәҶдёҖдәӣеү§зӣ®пјӣ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еҗҺе…¶дёӯзҡ„жҹҗдәӣеү§зӣ®еҘҪеғҸиҮӘеҠЁеҸҲдёҠжј”дәҶгҖӮ他们д»ҘеҫҖиҷҪдёҚдәҶи§Јиҝҷдәӣжғ…еҶөпјҢеҚҙд№ҹжІЎжңүиЎЁзӨәд»Җд№ҲгҖӮжҲ‘зҗҶи§ЈжҳҜ他们зҡ„еҘҪжҒ¶иҮ§еҗҰеҹәжң¬дёҠжІЎжңүеҸ—еҲ°жӯӨзӮ№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他们зҡ„вҖңжҢ‘еү”вҖқдё»иҰҒйӣҶдёӯеңЁд»ҘдёӢеҮ 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ҡ
гҖҖгҖҖйҰ–е…ҲпјҢ他们дёҚиөһжҲҗз¬јз»ҹең°и®Өдёәдј з»ҹдә¬еү§жҳҜдј ж’ӯ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зҡ„гҖӮ他们жҺҘи§ҰеҲ°зҡ„жҲ–иҷҪжІЎзңӢиҝҮеҚҙеҗ¬иҜҙзҡ„и®ёеӨҡдёҺеҺҶеҸІе’ҢеҺҶеҸІдәәзү©жІҫиҫ№зҡ„еү§зӣ®пјҢйҷӨе°‘ж•°иҖҢеӨ–пјҢеӨ§йғҪдёҺ他们жҺҢжҸЎзҡ„жӯЈеҸІжқҗж–ҷзӣёеҺ»з”ҡиҝңгҖӮжңүзҡ„жҳҜеј еҶ жқҺжҲҙпјҢжңүзҡ„жҳҜд»»ж„ҸжҠҪжҚўдёҺж·»еҠ пјҢжңүзҡ„йҮҚиҰҒе…іиҠӮе’Ңдәәзү©е№Іи„ҶжҳҜеӯҗиҷҡд№ҢжңүгҖӮиҖҢе…¶дёӯзҡ„дёҖдәӣйӘЁе№Іжғ…иҠӮе’Ңдәәзү©иҝҳз”ҡе…ізҙ§иҰҒпјҢз»қйқһжҳҜж— жүҖи°“зҡ„йҷӘиЎ¬гҖӮеҰӮжһңиҝҮеӨҡең°е°Ҷе®ғ们иҜҙжҲҗжҳҜвҖң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вҖқпјҢжңӘеҝ…дјҡдә§з”ҹйў„жңҹзҡ„ж•ҲжһңгҖӮиҖҢдё”жӯӨзұ»жғ…еҶөпјҢеҫҖеҫҖеҮәзҺ°еңЁдёәж•°дёҚе°‘д№ҹз”ҡе…·еҪұе“Қзҡ„еү§зӣ®дёӯпјҢеҰӮвҖңжқЁе®¶е°ҶвҖқзі»еҲ—еҸҠе…¶жңүе…ізҡ„еү§зӣ®гҖӮеҜ№з…§жӯЈеҸІпјҢйҷӨдәҶдәӢжғ…зҡ„дё»зәҝе°ҡжңүдёҖе®ҡеҸІе®һдҫқжҚ®пјҢйғЁеҲҶдәәзү©пјҲеҰӮжқЁз»§дёҡгҖҒжқЁе»¶жҳӯгҖҒжқЁж–Үе№ҝпјүе°ҡжңүе…¶дәәиёӘеҪұпјҢеҫҲеӨ§йғЁеҲҶеқҮдёәиҷҡжһ„пјҢжңүзҡ„иҝһиҫҲеҲҶйғҪеј„ж··дәҶпјҲеҰӮжқЁе»¶жҳӯдёҺвҖңжқЁе®—дҝқвҖқгҖҒжқЁж–Үе№ҝзҡ„е…ізі»е°ұжҳҜеҰӮжӯӨпјүпјҢиҮідәҺвҖңжҢӮеё…вҖқгҖҒвҖңеҮәеҫҒвҖқжӣҙдёәйҡҸж„ҸпјҢдёҖдјҡе„ҝиҝҷдёӘжҢӮеё…пјҢдёҖдјҡе„ҝйӮЈдёӘжҢӮеё…пјҢзӣҙеҲ°з”·дәәйҳөдәЎж®Ҷе°ҪиҖҢвҖңеҚҒдәҢеҜЎеҰҮеҫҒиҘҝвҖқзӯүзӯүгҖӮиҮідәҺдёҺе…¶жңүе…ізҡ„еҸҚйқўдәәзү©еҰӮжҪҳд»ҒзҫҺгҖҒжҪҳжҙӘзӯүпјҢеә”еҪ“жҳҜеҺҶеҸІдәәзү©жҪҳзҫҺзҡ„йҷ„дјҡдёҺ移жӨҚпјҢд№ҹдёҺеҸІе®һеӨҡжңүи·қзҰ»гҖӮеңЁиҝҷж–№йқўпјҢжҲ‘жҺҘи§Ұзҡ„иҝҷдәӣе№ҙиҪ»дәәиҮӘжңү他们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ҡ他们и®ӨдёәжҲ‘еӣҪдј з»ҹзҡ„вҖңиҜҙд№Ұе”ұжҲҸвҖқдәәеңЁиҷҡжһ„дёҠеӨ§иғҶеҫ—йқһеёёеҮәж јпјҢе…¶е®һдҪңдёәдёҖз§Қж•…дәӢеү§еҲӣдҪңе№¶ж— дёҚеҸҜпјҢдҪҶжҲ‘们дҪңдёәеҗҺд»ЈдәәдёҚеҝ…иҝҮдәҺејәи°ғе®ғ们зҡ„еҺҶеҸІд»·еҖјпјҢжӣҙдёҚеҝ…еӨёеӨ§е…¶дёәеҺҶеҸІж•ҷ科д№ҰпјҢзӣёеҸҚеҖ’жҳҜжңүиҙЈд»»иҝӣиЎҢйҖӮеҪ“еј•еҜјгҖӮе®ғ们并йқһдёҘж ј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жңүзҡ„дәәзү©еҸӘжҳҜжҹҗз§Қз¬ҰеҸ·пјҢжҲ–иҖ…жҳҜйҷ„зқҖеңЁеҸІе®һзәҝзҙўдёҠзҡ„ж•…дәӢеү§гҖӮиҮідәҺе®ғ们表зҺ°дәҶд»Җд№ҲжҖқжғідё»йўҳпјҢеҸҲеҪ“еҲ«и®әгҖӮиҝҷйҮҢпјҢжҲ‘дёҚиғҪдёҚжҸҗеҸҠдёҺжҲ‘дёҖиө·зңӢжҲҸгҖҒдҪ“дјҡжҲҸзҡ„иҝҷдәӣе№ҙиҪ»дәәеҲ«еҮәеҝғиЈҒзҡ„жҖқи·ҜпјҡжҲ‘жң¬д»Ҙдёә他们дјҡе°ҶдёҠдё–зәӘдә”е…ӯеҚҒе№ҙд»ЈйўҮеҸ—йқһи®®зҡ„гҖҠеӣӣйғҺжҺўжҜҚгҖӢдҪңдёә他们жүҖжҢҒи§ӮзӮ№зҡ„е…ёеһӢпјҢ然иҖҢ他们еҚҙи®ӨдёәпјҡиҝҷеҮәжҲҸд№ҹи®ё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дёәе®Ңе…Ёи·іеҮәдәҶеҸІе®һзҡ„зӘ иҮјпјҢиҖҢжҲҗдёәдёҖеҮәе®Ңж•ҙзҡ„жғ…иҠӮеү§гҖҒдәәзү©жғ…ж„ҹеү§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иЎЁйқўдёҠзҡ„жӮІеү§иүІеҪ©дёӯе®һеҲҷеёҰжңүжө“йҮҚзҡ„е–ңеү§жҲҗеҲҶпјҢдҪҝ他们зңӢдәҶпјҢдёҚиҮӘи§үең°дёҺдёҖиҲ¬зҡ„вҖңжқЁе®¶е°ҶвҖқзі»еҲ—еү§еүҘзҰ»ејҖжқҘгҖӮиҝҷиҜҙжҳҺ他们并йқһд»Ҙж•ҷжқЎзҡ„зңје…үеҺ»иҰҒжұӮдҪңе“Ғзҡ„еҺҶеҸІзңҹе®һпјҢиҖҢеҸҚж„ҹзҡ„жҳҜе°Ҷе®ғ们硬еҫҖвҖңеҺҶеҸІзҹҘиҜҶвҖқдёҠжӢүгҖҒйқ иҖҢе·ІгҖӮ
гҖҖгҖҖжӣҙзҰ»и°ұзҡ„дёҖзұ»еү§зӣ®еҰӮвҖңи–ӣе№іиҙөвҖқзі»еҲ—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гҖҠеӨ§зҷ»ж®ҝгҖӢпјҢиҜҙзҡ„жҳҜе”җе°Ҷи–ӣе№іиҙөеңЁиҘҝеҮүеӣҪеҪ“дәҶеӣҪзҺӢпјҢвҖңжқҖвҖқеӣһе”җжңқпјҢеЁҒйЈҺе…«йқўпјҢзӯүеҫ…д»–еҚҒе…«е№ҙзҡ„зҺӢе®қй’Ҹд№ҹеҫ—еҲ°е°ҒеҗҺд№ӢдҪҚпјҢдёҺиҘҝеҮүеӣҪзҡ„д»ЈжҲҳе…¬дё»еҗҢдҫҚи–ӣзҺӢпјҢеӨ§зҷ»ж®ҝиҖҢзҡҶеӨ§ж¬ўе–ңгҖӮи–ӣе№іиҙөдҪ•и®ёдәәд№ҹпјҹжҳҜи–ӣд»Ғиҙөзҡ„иҪ¬иә«пјҹдҪҶз»ҸеҺҶжғ…иҠӮд№ҹе·®ејӮжһҒеӨ§гҖӮйӮЈд№ҲеҸҲжҳҜи°ҒпјҹеҸӘиғҪиҜҙжҳҜеңЁиҷҡжһ„зҡ„йҒ“и·Ҝиө°еҫ—еҝ’иҝңгҖӮдҪҶеҗҢж ·д№ҹдҪңдёәдјјжҳҜиҖҢйқһзҡ„еҺҶеҸІеү§зҡ„йқўзӣ®еҮәзҺ°пјҢдҪҝдәәиҙ№и§Јзҡ„жҳҜпјҡж„ҲжҳҜзҰ»еҸІе®һз”ҡиҝңзҡ„вҖңеҺҶеҸІеү§вҖқпјҢж„ҲжҳҜдёәжј”еҮәиҖ…жүҖйқ’зқҗгҖӮгҖҠеӨ§зҷ»ж®ҝгҖӢзӣ®еүҚдёҠжј”зӣӣеҶөзҒ«зӮҪпјҢиҖҢдё”жңүеҗ„дёӘжөҒжҙҫдәүжј”гҖӮдёҺжқЁе®¶е°Ҷжңүе…ізҡ„еү§зӣ®дёҚд»…жңүиӢҘе№Ідј з»ҹеү§зӣ®пјҢи§Јж”ҫеҗҺзҡ„ж–°зј–еӨ§жҲҸд№ҹйқһжӯўдёҖеҮәгҖӮйӮЈдәӣе№ҙиҪ»зҡ„дә¬еү§жҺўзҙўиҖ…й—®жҲ‘дёәд»Җд№ҲпјҢжҲ‘дёҖж—¶д№ҹжғідёҚеҮәзЎ®еҲҮзҡ„зӯ”жЎҲгҖӮ
гҖҖгҖҖе…¶ж¬ЎжҳҜдј з»ҹйҒ“еҫ·ж•ҷиӮІй—®йўҳгҖӮеҰӮдёҠжүҖиҜҙпјҢдә¬еү§и®ёеӨҡеү§зӣ®дёӯи•ҙеҗ«зқҖзҡ„з§ҜжһҒжӯЈйқўзҡ„жҖқжғійҒ“еҫ·еӣ зҙ иҝҷйҮҢдёҚеҶҚиөҳиҝ°пјҢдҪҶеҚідҪҝжңүдәӣжң¬жқҘжҜ”иҫғе…·жңүиүҜжҖ§еӣ зҙ зҡ„еү§зӣ®пјҢд»”з»ҶеҲҶжһҗжҖқжғіеҶ…ж¶өд№ҹзӣёеҪ“иҠңжқӮпјҢз»ҸеёёеҮәзҺ°еүҚеҗҺдёҚеҗҢ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еҰӮи–ӣе№іиҙөе’ҢзҺӢе®қй’Ҹзҡ„зі»еҲ—еү§пјҢжң¬жқҘеңЁгҖҠеҪ©жҘјй…ҚгҖӢпјҲжҲ–з§°гҖҠдёүеҮ»е ӮгҖӢпјүгҖҒгҖҠеҲ«зӘ‘гҖӢзҡ„жҠҳеӯҗжҲҸдёӯиЎЁзҺ°дәҶдёҚд»ҘеҜҢиҙөеҸ–иҲҚиҖҢеңЁзңҹзҲұзӣёи°җзҡ„зҫҺеҘҪе“ҒжҖ§пјҢдҪҶеҲ°жңҖеҗҺзҡ„гҖҠеӨ§зҷ»ж®ҝгҖӢпјҢеҪ“иҚЈеҚҺеҠ иә«пјҢиҝҳжҳҜйӮЈдёӘзҺӢе®қй’Ҹд№ҹз«Ӣ马表зҺ°еҮәе–ңжһҒж„Ҹж»Ўд№Ӣе§ҝпјҢз”ұжӢ’дҝ—иҖҢйҡҸдҝ—пјҢе”ұеҮәдәҶвҖңдёҚж–©жҲ‘зҲ¶иҝҳиҰҒе°Ғе®ҳвҖқзҡ„иҮӘеҫ—д№ӢжҖҒгҖӮеүҚеҗҺеҜ№з…§пјҢи§ЈйҮҠдёәжҖ§ж јиҪ¬жҚўпјҢжҖ»е«ҢжңүдәӣзүөејәгҖӮеҸҲеҰӮгҖҠйҒҮзҡҮеҗҺВ·жү“йҫҷиўҚгҖӢдёӯзҡ„жқҺеҗҺпјҢж•…дәӢд№ӢеҲқпјҲдё”дёҚиҜҙеҸІе®һдёәдҪ•пјүеҘ№иў«еҲҳеҰғе’Ңйғӯж§җи°—е®іпјҢйҖғеҮәдә¬еҹҺпјҢиӢҰеұ…еҜ’зӘ‘пјҢеҗҺйҒҮеҢ…е…¬з”іжҳҺеҶӨжғ…иҖҢиў«иҝҺеӣһдә¬еҹҺгҖӮе…¶йҒӯйҒҮжң¬еҫҲдҪҝдәәеҗҢжғ…пјҢдҪҶеҪ“еҘ№еӣһдә¬еҹҺйҖ”дёӯпјҢе°ҡжңӘиҮіе®«дёӯпјҢеҚіе”ұеҮәпјҡвҖңеҫ…зӯүеӨ§дәӢе®үжҺ’е®ҡпјҢжҲ‘жҠҠдҪ зҡ„е®ҳиҒҢе°ұеҫҖдёҠеҚҮгҖӮвҖқжүҖжңүиҝҷдәӣпјҢж— йқһжҳҜйҖҸе°„еҮәзҡҮжқғзҡ„е…үеҪұжүҖеҸҠпјҢзәөжҳҜиў«еҺӢжҠ‘被摧жҠҳзҡ„е…ізі»дәәпјҢд№ҹйҡҫйҖғвҖңдёҖйҳ”еҝғжҖҒе°ұеҸҳвҖқзҡ„жҖӘеңҲгҖӮеҪ“жҲ‘зҡ„е№ҙиҪ»жңӢеҸӢ们зңӢеҲ°жӯӨеӨ„пјҢжҜҸжҜҸйҒ—жҶҫең°иҪ»иҪ»ж‘ҮеӨҙпјҢе°Ҫ管他们йқһеёёзҗҶи§ЈеҪ“е№ҙзҡ„еү§дҪңиҖ…йҡҫд»Ҙж‘Ҷи„ұзҡ„ж—¶д»ЈеұҖйҷҗжҖ§гҖӮ
гҖҖгҖҖд»ҘдёҠжүҖдёҫиҖ…иҝҳжҳҜвҖңжҲҸйӘЁвҖқдёҚй”ҷеҸӘжҳҜзЁҚе«ҢиҠңжқӮзҡ„еү§зӣ®пјҢиҖҢеҸҰжңүдёҖдәӣеү§зӣ®еңЁжҖқжғіеҶ…е®№дёҠеҚідҪҝд»ҘжңҖе®Ҫе®Ҹзҡ„е°әеәҰиЎЎйҮҸпјҢй—®йўҳд№ҹжҳҜжҳҺж‘ҶзқҖзҡ„гҖӮд»…дёҫеҮ дҫӢпјҢеҰӮгҖҠжёёйҫҷжҲҸеҮӨгҖӢеңЁзҺ°еңЁдә¬еү§иҲһеҸ°дёҠзӣёеҪ“жҙ»и·ғпјҢж„ҹи§үдёҠд№ҹжңүдәүжј”д№ӢеҠҝпјҢиҝҳжңүдәәзҫҺеҢ–жӣ°пјҡвҖңиЎЁзҺ°дәҶзҡҮеёқдёҺжҷ®йҖҡж°‘еҘід№Ӣй—ҙзҡ„зҲұжғ…ж•…дәӢгҖӮвҖқе…¶е®һеү§дёӯдәәзү©жҳҺжӯҰе®—жӯЈеҫ·еңЁ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ҠеҸҜз®—жҳҜйЎ¶е°–зҡ„иҚ’е”җж— еәҰзҡ„дё»е„ҝпјҢеҶ¶жёёжұҹеҚ—гҖҒе®ЈпјҲеәңпјүеӨ§пјҲеҗҢпјүиҖҢзәөжғ…ж·«д№җпјҢеұ…вҖңиұ№жҲҝвҖқиҖҢжҲҗдёәеҸҳжҖҒзҺ©е®¶гҖӮеҸӘжҳҜеӣ дёәеҪ“ж—¶жҳҺзҺӢжңқж°”ж•°жңӘе°ҪпјҢиҷҪ然еҸ‘з”ҹдәҶеҲҳе…ӯгҖҒеҲҳдёғеҶңж°‘еӨ§иө·д№үпјҢиҝҷдёӘжңұеҺҡз…§дҫҘе№ёжІЎжңүйҒӯеҲ°йҡӢзӮҖеёқжқЁе№ҝйӮЈж ·еҪ“дё–иў«жҺЁзҝ»зҡ„е‘ҪиҝҗгҖӮдјјжӯӨдё»е„ҝпјҢдёҚзҹҘиЎЁжј”иө·жқҘжңүдҪ•зҫҺж„ҹпјҢеҸҲжңүдҪ•зңҹзҲұеҸҜиЁҖпјҹеҪ“е№ҙзҡ„иҖҒжң¬еӯҗдёӯпјҢеҪ“е№ҙжқҺеҮӨе§җи·ӘдёӢи®Ёе°Ғж—¶пјҢжӯЈеҫ·е”ұйҒ“пјҡвҖңеӯӨдёүе®«е…ӯйҷўйғҪе°Ғе°ҪпјҢе°ҒдҪ дёәй—ІжёёжҲҸиҖҚе®«гҖӮвҖқгҖҠжёёйҫҷжҲҸеҮӨгҖӢеңЁиҲһеҸ°дёҠзҡ„жҙ»и·ғпјҢдёҺиҝ‘е№ҙжқҘе…ҙиө·зҡ„еҪұи§ҶеұҸ幕дёҠвҖңзҡҮйЈҺеҠІеҗ№вҖқдёҚиғҪиҜҙжІЎжңүдёҖе®ҡиҒ”зі»пјҢд№ҹи®ёжңүдәәи®Өдёәиҝҷзұ»еү§зӣ®еҸҜиғҪдјҡеҗёеј•и§Ӯдј—пјҢе…¶е®һйӮЈиҰҒзңӢд»Җд№Ҳж ·зҡ„и§Ӯдј—гҖӮжҲ‘зҡ„е№ҙиҪ»жңӢеҸӢ们зңӢдәҶжңұеҜ№жқҺзҡ„жҢ‘йҖ—ж—¶иҜҙпјҡвҖңе°ұеғҸеҗғдәҶдёҖеҸӘиӢҚиқҮпјҒвҖқеҸҰеҰӮгҖҠжі•й—ЁеҜәгҖӢпјҢеү§дёӯдәәзү©еӮ…жңӢеңЁдёҖеңәзә·зәӯзҡ„жЎҲ件дёӯе°ҸеҸ—зүөиҝһпјҢеҚҙжңҖз»ҲиҺ·еҫ—еЁҮеҰ»зҫҺеҰҫпјҢжӢҘжңүдәҢе§ЈпјҲе®Ӣе·§еЁҮгҖҒеӯҷзҺүе§ЈпјүеҗҢдҫҚпјҢиүізҰҸйқһеёёгҖӮиҝҷдәӣпјҢйғҪжҳҜиҝҮеҺ»дёӯеӣҪз”·дәәзҡ„зҗҶжғівҖңж јеұҖвҖқпјҢд№ҹжҳҜиҝҮеҺ»дә¬еү§еү§жң¬дёӯ并йқһдёӘеҲ«зҡ„жғ…иҠӮе®үжҺ’гҖӮ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еү§зӣ®пјҢйҷҗдәҺзҜҮе№…дёҚиғҪдёҖдёҖеҲҶи§ЈгҖӮз®ҖиЁҖд№ӢпјҢеӨ§иҮҙеҢ…жӢ¬йқһеҗҢдёҖиҲ¬ең°е®Јжү¬зҡҮжқғиҮідёҠиҖҢж„ҡеҝ иҮіиҙөпјӣиөһиөҸиҮЈдёӢжҲ–е№іж°‘иў«еҮҢиҷҗе°ҡдёҚиҮӘзңҒиҖҢж„ҹжҲҙдёҮеҲҶпјӣдёҚеҠ еҲҶжһҗең°е°ҶеҸҚжҠ—еҺӢиҝ«зҡ„еҠӣйҮҸж–Ҙд№ӢдёәиҙјпјҢиҖҢйўӮжү¬еҠ©зәЈдёәиҷҗзҡ„й№°зҠ¬дёәд№үеЈ«иҙӨиғҪпјӣеҜ№е°Ғе»әд№ дҝ—йҷӢиЎҢиЎЁзӨәиүізҫЎиҖҢжӯЈйқўжҺЁеҠ©пјҢзӯүзӯүгҖӮеә”иҜҘиҜҙпјҢйғҪеұһдәҺдә¬еү§ж–Үжң¬дёӯзҡ„з‘•з–өгҖӮ
гҖҖгҖҖдә¬еү§е°ұжҳҜдә¬еү§
гҖҖгҖҖз»јдёҠ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ҡжүҖи°“дә¬еү§зҡ„йҒ“еҫ·еҶ…ж¶ө既然жҳҜ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жүҖеҪўжҲҗпјҢеҝ…е®ҡдҝқжңү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дјҰзҗҶеҶ…ж ёгҖӮеҚідҪҝдёҺд»ҠеӨ©жҲ‘们жүҖйңҖиҰҒзҡ„йҒ“еҫ·еҸ–еҗ‘йҮҚеҗҲпјҢд№ҹеҸӘиғҪиҜҙе®ғеңЁдёҚеҗҢж—¶д»ЈжңүзӣёиҝһжҺҘзӣёз»§жүҝзҡ„дёҖйқў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®Ңе…ЁжІЎжңүеҝ…иҰҒжңҹжңӣдә¬еү§жӢ…еҪ“йҒ“еҫ·ж•ҷеҢ–иҖ…зҡ„йҮҚиҙҹгҖӮеӣ дёәдә¬еү§жҳҜдёҖй—ЁеҸӨиҖҒзҡ„иүәжңҜпјҢдә¬еү§е°ұжҳҜдә¬еү§гҖӮеҪ“然пјҢеҪўжҲҗдәҺе°Ғе»әж—¶д»Јжң«жңҹзҡ„дә¬еү§пјҢе…¶дј з»ҹжҖқжғізҡ„вҖңеҺҹжұҒвҖқжңүзҡ„жҳҜйҷҲи…җзҡ„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дё‘йҷӢзҡ„пјӣдҪҶжңүзҡ„并дёҚйӮЈд№Ҳдё‘пјҢз”ҡиҮіиҝҳжңүеҮ еҲҶзҫҺгҖӮеҰӮгҖҠдёүеЁҳж•ҷеӯҗгҖӢпјҢеҘ№зҡ„вҖңе®ҲиҠӮвҖқдёҺвҖңж•ҷеӯҗвҖқеӣә然еқҡе®Ҳзҡ„жҳҜе°Ғе»әйҒ“еҫ·пјҢдҪҶеҘ№йҹ§жҖ§е®үиҙ«пјҢж•ҷеӯҗвҖңеӯҰеҘҪвҖқиҝҳжҳҜжңүеҮ еҲҶжӯЈж°”еңЁгҖӮеӣ иҖҢжҲ‘зҡ„е№ҙиҪ»жңӢеҸӢ们д№ҹиғҪжҺҘеҸ—гҖӮ
гҖҖгҖҖеҶҚиҖ…пјҢжҳҜеҜ№еҫ…дә¬еү§зҡ„жҖҒеәҰй—®йўҳгҖӮиҝҮеҺ»жҹҗдёӘж—¶й—ҙж®өз”ұдәҺ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пјҲеҢ…жӢ¬йҳ¶зә§ж–—дәүпјүзҡ„еӣ зҙ д»Ӣе…ҘпјҢиҝҮдәҺиӢӣжұӮд№ғиҮіжҢҮж–ҘеӣәжңүдёҚеҪ“пјҢдҪҶеҰӮеҚ•зәҜеҪ’дёәеЁұд№җжҖ§иҖҢдёҚи®Ўе…¶е®ғд№ҹжңӘеҝ…е…ЁйқўгҖӮиҝҷйҮҢдёҫдёҖдёӘдҫӢеӯҗгҖӮеӨҡеҗ¬дәәиЁҖпјҢиҜҙйҖўе№ҙиҝҮиҠӮеёёжј”гҖҠйҫҷеҮӨе‘ҲзҘҘгҖӢжҳҜвҖңеӣҫдёӘеҗүеәҶвҖқгҖӮдёәдҪ•пјҹеҫҲжҳҫ然жҳҜеӣ дёәжңүвҖңйҫҷвҖқдёҺвҖңеҮӨвҖқд№Ӣй…Қд№ҹгҖӮеҰӮжҳҜдёҖиҲ¬е№іж°‘з»“е©ҡеҲҷдёҚеӨҹе‘іе„ҝпјҢе”ҜзҡҮдёҠжҲ–еҫ…еҒҡзҡҮеёқзҡ„иҙөиғ„дёҺйҮ‘жһқзҺүеҸ¶зҡ„е…¬дё»д№Ӣзұ»жҲҗе©ҡжүҚиғҪдҪҝдёҮж°‘еҗҢд№җвҖңе‘ҲзҘҘвҖқгҖӮдёҚжҳҜеҗ—пјҹжүҖд»ҘпјҢеҪ“дёҖдҪҚжҜ”иҫғеҶ…иЎҢзҡ„е№ҙиҪ»жңӢеҸӢй—®жҲ‘пјҡдёәд»Җд№ҲзҺ°еңЁдёҚеӨ§з”ЁгҖҠз”ҳйңІеҜәгҖӢиҖҢеҮ д№ҺдёҖеҫӢз”Ёе®ғзҡ„еҲ«еҗҚгҖҠйҫҷеҮӨе‘ҲзҘҘгҖӢе‘ўпјҹжҲ‘笑зӯ”пјҡеҸҜиғҪеӣ дёәжҳҜе…Ёжң¬еӨ§жҲҸд№Ӣж•…еҗ§гҖӮиҝҷйҮҢиҜҙжҳҺдәҶ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пјҡж–Үжң¬еӣә然жҳҜиҝҮеҺ»зҡ„пјҢеӨ§ж”№еҮ д№ҺдёҚеҸҜиғҪпјҢдҪҶеҜјгҖҒжј”д№ҹеә”жңүдёӘжӯЈзЎ®еҜ№еҫ…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иҰҒжұӮеҸӮдёҺжј”еҮәзҡ„дәәе‘ҳдҝқжҢҒжё…йҶ’еӨҙи„‘дәҰдёҚдёәиҝҮгҖӮжј”жҲҸеӣә然иҰҒжҠ•е…ҘпјҢиҰҒжңүж„ҹжғ…пјӣеҚҙд№ҹдёҚиғҪе…Ёж— зҗҶжҖ§гҖӮеҰӮдҪ•жҠҠжҸЎпјҢиЎЁзҺ°дәҶжј”еҮәдәәе‘ҳзҡ„ж°ҙе№іпјҢд№ҹзӣҙжҺҘеҪұе“ҚеҲ°жј”еҮәж•ҲжһңгҖӮж„ҹжғ…жҠ•е…ҘдёҺзӣІзӣ®жҖ§жҳҜдёӨеӣһдәӢпјҢдёҚеҸҜеӣ жҠҠжҸЎдёҚеҪ“еҠ еӨ§дәҶжҹҗз§Қиҙҹйқўж•Ҳеә”гҖӮ
гҖҖгҖҖж—©еүҚжңүдёӘж—¶жңҹпјҢдёҖиҲ¬и§Ӯдј—еҸҚжҳ дә¬еү§еҗ¬дёҚжҮӮпјҢдҪҶеӨҡеҚҠеҗ¬е”ұеҫ—еҘҪеҗ¬жү“еҫ—зғӯй—№иҝҳжңүвҖңйҒ®жҺ©вҖқзҡ„дёҖйқўгҖӮзҺ°еңЁзӣёжҜ”д№ӢдёӢеҗ¬жҮӮдәҶпјҢжҳҜеҘҪдәӢпјҢеҚҙд№ҹеӨҡдәҶдәӣвҖңжҢ‘еү”вҖқпјҢеҸӘеӣ дёәвҖңзңӢй—ЁйҒ“вҖқжқҘ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д»ҘеүҚеӨ§еҚҠжҳҜеӣ дёәдёҚеҘҪжҮӮгҖҒдёҚд№ жғҜпјҢеҪўжҲҗйҡ”иҶңиҖҢдҪҝи§Ӯдј—пјҲдё»иҰҒжҳҜе№ҙиҪ»дәәпјүеҜ№дә¬еү§дёҚеӨҹзғӯиЎ·пјӣд№ғиҮіжҮӮдәӣдәҶпјҢеҸҲеӨҡдәҶжҹҗдәӣеү§зӣ®зҡ„жҖқжғіеҶ…е®№йҷҲи…җгҖҒж ји°ғдёҚйҖӮгҖҒж°”е‘іеҲ«жүӯзӯүеҺҹеӣ иҖҢз–ҸзҰ»дә¬еү§гҖӮиҝҷдёҖзӮ№жҳҜеҗҰдҪҝеҶ…иЎҢ们е§Ӣж–ҷдёҚеҸҠе‘ўпјҹж”№иҝӣзҡ„йҖ”еҫ„еӣәжңүи®ёеӨҡпјҢдҪҶйҰ–иҰҒзҡ„жҳҜиҰҒжңүжӯЈзЎ®зҡ„еј•еҜјпјҢдёҚжҳҜдёҚйҖӮеҪ“зҡ„иҜҜеҜјпјҢе®һдәӢжұӮжҳҜпјҢйҮҚеңЁиүәжңҜпјҢжңҖеҝҢдёҚиғҪжҙҘжҙҘд№җйҒ“иҙҹйқўйғЁеҲҶиҖҢеј•иө·еҸҚж„ҹгҖӮеҪ“然пјҢеҰӮиғҪз«ҷеңЁжӣҙй«ҳи§’еәҰпјҢжү¬й•ҝйҒҝзҹӯпјҢд»ҺеҶ…е®№еҲ°еҪўејҸжӯЈзЎ®дҝ®ж”№иҖҢеҸҲдёҚдјӨе…¶йӘЁпјҢеҲҷжҳҜдә¬еү§иүәжңҜд№ӢеӨ§е№ёд№ҹгҖӮ
|
| |
| | |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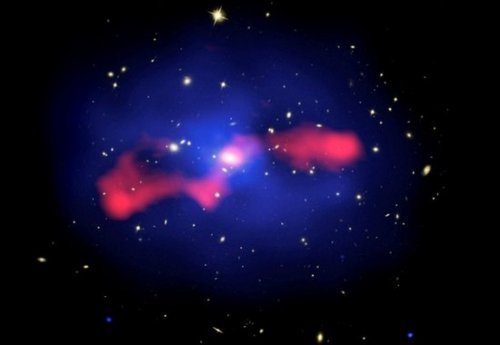

.jpg)




.jpg)





